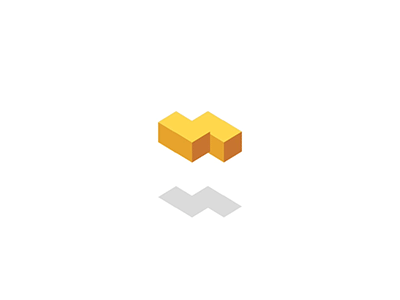+-


前辈的学者常以学问的趣味启迪后生,因为他们自己实在是得到了学问的趣味,故不惜现身说法,诱导后学,使他们也在愉快的心情之下走进学问的大门。例如,梁任公(梁启超)先生就说过:“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任公先生注重趣味,学问甚是渊博,而并不存有任何外在的动机,只是“无所为而为”,故能有他那样的成就。
一个人在学问上果能感觉到趣味,有时真会像是着了魔一般,真能废寝忘食,真能不知老之将至,苦苦钻研,锲而不舍,在学问上焉能不有收获?不过我尝想,以任公先生而论,他后期的著述如历史研究法,先秦政治思想史,以及有关墨子佛学陶渊的作品,都可说是他的一点“趣味”在驱使着他,可是在他在年青的时候,从师受业,诵读典籍,那时节也全然是趣味么?作八股文,做试贴诗,莫非也是趣味么?我想未必。大概趣味云云,是指年长之后自动作学问之时而言,在年青时候为学问打根底之际恐怕不能过分重视趣味。学问没有根底,趣味也很难滋生。任公先生的学问之所以那样的博大精深,涉笔成趣,左右逢源,不能不说一大部分得力于他的学问根底之打得坚固。
我尝见许多年青的朋友,聪明用功,成绩优异,而语文程度不足以达意,甚至写一封信亦难得通顺,问其故则曰其兴趣不在语文方面。又有一些位,执笔为文,斐然可诵,而视数理科目如仇雠,勉强才能及格,问其故则曰其情趣不在数理方面,而且他们觉得某些科目没有趣味,便撇在一旁视如敝屣,怡然自得,振振有辞,略无愧色,好象这就是发扬趣味主义。殊不知天下没有没有趣味的学问,端视吾人如何发掘其趣味,如果在良师指导之下按部就班的循序而进,一步一步的发现新天地,当然乐在其中,如果浅尝辄止,甚至躐等躁进,当然味同嚼蜡,自讨没趣。一个有中上天资的人,对于普通的基本的文理科目,都同样的有学习的能力,绝不会本能的长于此而拙于彼。只有懒惰与任性,才能使一个人自甘暴弃的在“趣味”的掩护之下败退。
自小学到中学,所修习的无非是一些普通的基本知识。就是大学四年,所授课业也还是相当粗浅的学识。世人常称大学为“最高学府”,这名称易滋误解,好象过此以上即无学问可言。大学的研究所才是初步研究学问的所在,在这里作学问也只能算是粗涉藩篱,注重的是研究学问的方法与实习。学无止境,一生的时间都嫌太短,所以古人皓首穷经,头发白了还是在继续研究,不过在这样的研究中确是有浓厚的趣味。
在初学的阶段,由小学至大学,我们与其倡言趣味,不如偏重纪律。一个合理编列的课程表,犹如一个营养均衡的食谱,里面各个项目都是有意而必要的,不可偏废,不可再有选择。所谓选修科目也只是在某一项目范围内略有拣选余地而已。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犹如一个科班出身的戏剧演员,在坐科的时候他是要服从严格纪律的,唱工做工武把子都要认真学习,各种角色的戏都要完全谙通,学成之后才能各按其趣味而单独发展其所长。学问要有根底,根底要打得平整坚实,以后永远受用。初学阶段的科目之最重要的莫过于语文与数学。语文是阅读达意的工具,国文不通便很难表达自己,外国文不通便很难吸取外来的新知。数学是思想条理之最好的训练。其他科目也是各有各的用处,其重要性很难强分轩轾,例如体育,从另一方面看也是重要得无以加复。总之,我们在求学时代,应该暂且把趣味放在一旁,耐着性子接受教育的纪律,把自己锻炼成为坚实的材料。学问的趣味,留在将来慢慢享受一点也不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