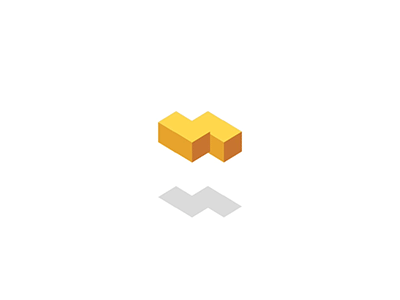+-


屈指一算,我今年67岁,提起我的学历,不怕人笑话,我只在学校读了六年书。然而不知什么原因,我从小就喜欢阅读。多少年来,只要我闲下来没事,就想读点东西,不论是一本书,或是一本杂志,即使是眼前只有一张旧报纸,我都能静下心来从头到尾把它读完。
小时候家里只有父亲每月30多元钱的工资,却要养活一家四口人,无钱给我和妹妹买课外读物。如果我和妹妹能从父母那里要到几分钱,到小摊上看几本小人书,那就是我俩最高兴的事了。
1963年夏天,我读小学三年级时,我家从四川平武县城龙安镇西街一户私人深宅搬到南街居住。南街的住房是公房,紧挨古城墙南门,一抬头就能看见明朝宣德五年(1430)修筑的古城墙,城门上随风飘拂的莎草中“清平”两字清晰可见。一出城门,下面就是奔腾的涪
江。南街的住房前后共有四间,每月的房租是两元钱。和以前私人住房一比,公租房不仅价钱便宜,而且面积大、房间多。经母亲安排,最后一间做厨房,当中两间为睡房,临街的一间是堂屋。当搬完家,母亲高兴地说:“哎呀,儿呢,我家终于有堂屋了!”那时的堂
屋不仅是客厅,而且是一家人吃饭和小孩做作业的屋子。很快,我和母亲将一张旧四方桌摆在中间,周围放上四个高板凳。母亲看了一眼四周的墙壁说:“唉,太破旧了,得用报纸把墙糊起来。”那时县城百姓住的公租房都是穿木结构没有楼层的小瓦房,墙壁的装修材
料主要是由竹条编成,然后抹上一层用稻草搅拌在一起的泥巴,外面涂的是薄薄一层石灰浆,时间长了,泥巴和石灰就会自然脱落。
一天下午,母亲从县政府旁边的废品站买回一大捆旧报纸,接着用面粉打了一盆糨子,我俩开始在堂屋里糊墙。母亲买回的旧报纸有《人民日报》《四川日报》《解放军报》《文汇报》《光明日报》等。在糊墙过程中,我不仅看见报纸的副刊上有发表的诗歌,而且还有
一些散文和杂文。当看到一首首好诗和一篇篇好文章时,我不知不觉停下手上的活儿。母亲看了一眼我和手上的报纸说:“哎呀,儿呢,你把报纸‘好看’的一面贴在外头,以后有时间再慢慢地看嘛。”我们一直干到天黑,终于将四周的墙壁糊好。母亲拉了一下电灯开
关,屋里顿时焕然一新。最后,母亲将一张崭新的毛主席像端端正正地贴在堂屋的正面墙上,微笑着说:“这才像个堂屋的样子嘛。”
自从墙上有了一首首好诗和好文章,我放学后就抓紧时间做作业,一做完作业就看墙上的“书”。夏季天长黑得晚,堂屋朝西临街光线好,每当夕阳落山前我总能在墙上看半个多小时的“书”。有的诗和文章贴得太高,于是我就站在高板凳上看;有些字不认识,我就查
字典。说实话,有些诗和文章我那时还不明白是啥意思。
冬季白天短,放学回到家,天已黑了。母亲为了省电费,我和妹妹在堂屋里一做完作业,她就把灯关了,并立即把我俩撵到厨房的火塘边去烤火。因此,我只能在白天“挤时间”看一下墙上的“书”。到了年底,我断断续续读完四面墙上的“书”。在川西北地区,过年
前有个辞旧迎新的习俗,那就是要“打扬尘”(即用长竹竿绑上扫把或鸡毛掸,除去屋子里的灰尘和蜘蛛网)。打完“扬尘”,母亲看了看堂屋四周叹口气说:“唉,就要过年了,想不到还不到一年时间,这墙上糊的报纸不仅有些地方脱落,而且已变得又黄又旧,得买
些报纸重新糊一遍。”我一听,不由得暗暗地高兴起来:因为墙上的“旧书”我已看完,又可以看“新书”了。
从三年级到六年级,我不仅从“书墙”上读到了闻捷、阮章竞、贺敬之、郭小川、柯岩、李瑛等著名诗人在报刊上发表的诗歌,而且还读到曹靖华、茅盾、丰子恺、沈从文、巴金、杨朔等著名作家发表的散文和杂文。记得1965年元月,就要过年了,因天气特别冷,涪江
处于枯水期,水流量很小,东门外涪江对岸的小水电站停止发电,一连半个多月县城的百姓只好点煤油灯照明,没想到这给了我“挑灯夜读”的机会。十几个夜晚,我拿着煤油灯在“书墙”上不仅阅读了闻捷的《我思念北京》、贺敬之的《西去列车的窗口》、柯岩的《
中国孩子的心》、袁鹰的《巴拿马,愤怒的河!》等人的诗歌;同时还读到曹靖华的《忆当年,穿着细事且莫等闲看!》、沈从文的《天安门前》,茅盾的《海南杂忆》等人的散文。有天晚上,夜已很深了,我站在高板凳上拿着煤油灯正在如醉如痴地阅读贺敬之的诗歌
《三门峡——梳妆台》时,没想到一只大老鼠从无顶棚的房梁上飞奔时突然“吱”的一声,从空中掉到我头上,顿时把我吓得从高板凳上摔了下来……
一晃,很多年过去,父母早已离开人世。然而,每当我想起童年在古城墙下老房子里“书墙”上读“书”的经历,总有一种甜蜜的味道在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