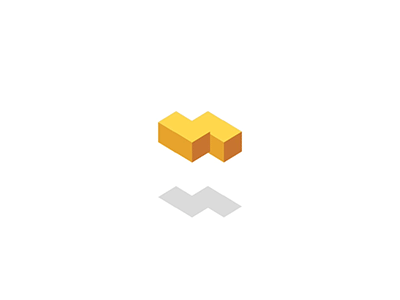+-

篇一:回乡记
星期天,兄弟姐妹一起六个回了趟乡下老家,看望患了尿毒症晚期的二妈。
开车,个把小时的路程,那熟悉的村落渐渐清晰起来。才下过一场雨,临近村子的小道泥泞不堪,乘坐的凯美瑞轿车几次打滑,车身被泥巴糊弄的分不清鼻孔眼睛。好在有惊无险,成功脱离困境了。因为曾经经历过小车陷在泥巴里不得动弹,不得不喊来亲戚八嘎帮忙推车,那悲壮悲催的场景,就像是一坨乌黑乌黑的阴影笼罩在大家伙的心头。
二爷二妈,是我爸爸的弟弟和弟妹。虽然爸爸已经不在了,但是二爷二妈,毕竟是我们最亲的长辈,不能割舍的血缘亲情啊。
二爷身体瘦削,头发花白苍老了很多。二妈更是,走路孱孱弱弱,脸色蜡黄,仿佛冬天里恍惚不定,微弱的没有能量的那一只烛火。
看着真是心里疼痛啊。
二妈一生勤劳节俭,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晚年了却罹患重病。医生说可以做放疗和化疗,以减轻痛苦,延缓生命,儿女们也这样建议支持。二妈却说:“这么大的年纪了,花那个冤枉钱不值得。再说做化疗也是很遭罪的事,人也受不起那个折磨了,不如安安逸逸,过一天算两个半天就行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想起总觉得还是很残酷。人操劳了一辈子,就这样眼睁睁被病魔夺了生命去?
想我们平时都借口太忙,忽略了她们的存在了。这次,专门给她买了新的衣服,水果,点心,牛奶等,并嘱咐说:“给您一点钱是我们的心意,您不要又舍不得花哟。”
二妈顿时老泪纵横:“我吃的有,穿的有,看见你们了,心里就高兴了·~~~~比吃了喝了还要高兴了~~~~~”叙叙说说老半天,二妈还情不自已,止不住地抬起衣袖揩着脸上皱褶里的眼泪花子。
“哎~~~~~~”我觉得,人生有时候真的只剩下一声叹息了。
回老家一趟,有一些亲戚也是要顺道去拜访一下的。
印象深刻,感触最多的是恩爹恩婆一家。恩婆今年84岁,耳朵背气的厉害,和她说话要凑拢了大声喊着才行。我心想,耳背,或许也是延年益寿最妙的的途径之一?因为,人一生听话太多,受气太多,免不了伤心动怒就折了寿,索性听不见,倒生活的简单快乐!
恩婆的媳妇也是60多岁的人,由于高血压中风,走路踉踉跄跄,似乎总找不到平衡点,一只手使劲挣扎,又感觉有力使不出的样子。一个大约两三岁,光着脚丫的调皮孙子在她膝盖上绕来绕去。
从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大约听懂了一些故事内容。恩爹,85岁,三个月前死了,死,终是一条遵循自然规律的事情,无可阻挡,但还是让人唏嘘。恩爹在一次码棉梗垛的时候,不小心从垛上摔了下来,遂瘫痪在床。几天后,家人发现,恩爹服了农药,了结了自己的一生(据说是一种喷洒棉花的助壮素,三支即可,瞬间封喉)。众人啧啧感慨说,恩爹一生太造业了,太让人想不得。
恩爹媳妇淡然地讲述,就像是发生在隔壁家的事情。偶尔,不堪忍受孙子的调皮捣蛋和骚扰,就露出极其倦烦的神情,又疼又恼地呵斥着:“自己去玩。”我不禁为这孩子暗捏了一把汗,因为刚就看到屋子旁边有一个长满了水草的大水塘,那水塘可是不讲人情地呢。
话题又关注起恩婆来,恩婆媳妇说:“她现在还好,可以招呼自己,如果哪天动不得了,她也跟自己想好了后路。”大家不可思议地问:“什么后路?难道她不怕死?”
恩婆媳妇也是熬成多年的婆了,可能,晚年的这场中风让她体验到了生不如死,欲罢不能的滋味,于是很了解,很无奈地说:“年纪大了,活着没啥意思了,一代管一代,我们都觉得是娃们的负担了~·~~~”
返程的路上,我大姐(今年55岁)幽幽地说了句:“恩婆80多岁,还有我们这些晚辈们来看她,等我老了,不晓得有没有哪个记得我哟。”
大嫂接话:“肯定有啊,你只怕也会一把鼻涕一把泪,拉着别个的手不放吧?”
二嫂惊醒似的,审视着自己的手说:“好像,恩婆刚把鼻涕弄到我手上了,粘之拉乎好不舒服。”
众人无不狂笑~~~~~~~
篇二:回乡记
父亲年逾古稀,一直想找个机会重返当年下放的地方,也即是我出生之处。条件稍好些,父亲便跟当时的村团支部书记、后来的村支部书记联系上,在镇圩上的路口等着驱车进入。
久未谋面,只是从别处找来的号码联系上。再见面,互相愣怔了半天,打量一番,才喊出彼此的名字。当时的村团支部书记、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早已满头华发,看似与父亲相差无几,精干的个子,幽默爽朗的话语,几句土话,拉回大家熟悉的感觉。
这是乡镇的入口处,需往里走二十几公里才能到达,必须经过三个村子。父亲一路上念叨着这是什么村,那是什么路,沿途有什么变化,那时的树没那么高,现在经过封山育林都长高长密了许多,岔路口那棵大榕树还在,一些老房子依然立着,依稀能看出当时的风貌。路上时不时碰上熟人,老支书不时从车上下来唠会儿嗑,抽支烟。山路崎岖,左拐右弯,上坡下坡,好在都是水泥路,村村通水泥路,交通便捷。越往里走,房子越稀少,树木越茂盛,坡坎也越多,弯道越来越崎岖。摇下车窗,满眼绿意,迎面扑来的是清新纯净的空气,夹杂着山野草木的清香,呼吸变得愈加舒畅,似乎是吸氧一般。车子行驶了三四十分钟,几处大山突兀在视野中,大山围拢怀抱中的村子便是父母魂萦梦牵了几十年的地方——赣南黄坡村。(中国- sanwen.aiisen.com)
这几十年,在父母的口中,这个地名出现的频率很高,但我一直未曾探访过。只是觉得是一个不相干的地方而已。而今真的出现在眼前,首先是觉得此地的特别。它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据说,除我们进山的水泥路外,还有三条土路四通八达,但需翻山越岭,它在四个乡镇的中心点,因为此地山最高,这片区域便成了真正的世外桃源:宁静、静谧、安逸、祥和。山中野猪、麂子经常出没,据父亲说,当初亲身经历麂子蹿过身边的事。远处山峰郁郁葱葱,树种繁多,尤以山脚下的毛竹居多,绿意盎然,一水的绿色,仿若可以拧出水来的透亮;一条小溪蜿蜒绕村而过,尤能见小鱼儿在游弋。在拥挤的城市群,在工业化的时代,污染源、重金属侵蚀水质日益严重的今天,能看到如此清澈的小溪流真是意外,这是仅存的一些原生态的阵地,退缩在大工业时代的一个角落,如同孩童的眸子那般天真与无邪;田里庄稼已经成熟,黄澄澄的,沉沉地挂坠枝头,一大片一大片的黄寓意着丰收与富足;溪边的果树高大茂盛,恣意地成长,在这,没有束缚,没有憋屈,这是一片沃土,有足够的根基与水分,向人们提供丰硕的果实。
车子开到村头,老支书迫不及待地下来,老支书也离开二十几年了,家中的房屋也早已圮毁,但一年至少回来一次祭祖烧纸。一下车,便碰上村小的校长,当年的村支书之子,也是父亲的学生,认了半天,惊讶地叫了起来,村子平日寂静,少有外人来,在四周劳作的几个妇女,被父母一个个叫出名字来,“代姣”“毛女”“谢姣”眼前的一个个黑瘦、精干的白发妇女从地里、田边、屋内闻讯立即围拢过来,故人相见,分外惊喜,辨认也花了一番工夫,互相打量,毕竟四十多年未见,当年年轻、各有特色的人物谱在眼前呈现,如今已是两鬓染霜、满头华发、面露沟壑、缺牙耳背的老人,这是怎样一种复杂的心境:当年高挑苗条、扯着大嗓门唱山歌的代姣,如今精瘦干瘪黑脸膛,一笑露出金灿灿的假牙,是她吗?当年刚当上新娘、梳着两条大黑亮辫子的、能干利落的谢姣,如今行动蹒跚、体型宽大,是她吗?当年反应敏捷、油嘴滑舌的仪姣,如今不露声色、佝偻着的,是她吗乡音还是那个乡音,只是面容苍老,岁月无情,在四十多年未见的脸上依稀残留着当时的音容笑貌。
大家拉着手走村串巷,在各家逗留,促膝长谈,交谈甚欢,有一种久别的喜悦、激动、兴奋。老支书带我们来到当年生我养我的地方,原来的土坯房屋子早已倾圮不复存在,旁边的屋子残存着当年的木窗,斑斑驳驳,土墙上爬满了南瓜、丝瓜藤,仔细辨认才依稀看得出它的面貌。父亲说,当年我妈在这生我的时候,是他亲自在烧水、伺候,而今当年那个呱呱落地的我,却已成了中年妇人,随夫携子。往右走的正厅门口,七零八落地堆了许多杂物,但两边的门联却依然清晰可辨,隶书体,红字,当年的热血口号“伟大的”父亲一眼认出,这是当年他手书的。
时空凝固在四十多年前,在这个僻静的小山村。
在那个火热的年代,穷乡僻壤里一下涌人了众多外来客。听说此地山清水秀,柴火不用外运,直接上山砍来即可;因为远离乡镇,这安静的一隅可以远离纷争。尽管有些人因路程偏远,交通不便,去了后回来就调整地方了。但父母却依旧无悔地选择这个地方,风景秀美,远离尘嚣。
父母在此待了五年,一个带队管理一些上海知青,一个在村小当教师。父亲当时二十五六岁,说是带队,但与知青们情如一家,在他看来,当时这些上海的孩子们十几岁、二十岁,风华正茂,豆蔻年华,刚从城市中来,闹了不少趣事:不会烧柴,差点把房子烧了;不会煮饭,水放少了,都成锅巴了。父亲也都很照顾他们,有女生不方便时,父亲会安排她们休息,遇有流氓调戏,合力抓起来教训;一起下田插秧,上山砍柴,样样农活,逐渐地熟练起来。当地民风淳朴,村支书和群众也很照顾他们,平时有些番薯、花生农产品都会分些给他们,生活上体贴细致人微,真正打成一片。
知青们在农村,向农民群众学习,体会到农事的不容易,也感受到农民的深情厚谊,水乳交融。直至现在,这班上海知青时常打听老支书等人的联系方式,还时常会回来看望他们,热情有加,一起回味当初那段难忘的经历。而母亲在这个山村里,客家人尊师重教的传统一直没有被当时的争斗所泯灭,对教师都是相当尊重,对文化知识是有着渴求与羡慕的。
当岁月的车轮驶过四十多年,这段经历相信在每个人的生活里都印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如火的青春,炽热的情怀,定格在这个门联上。
离开时还太小,才一两岁,但回来时却不觉得陌生,似曾相识。还是这个经度,这个纬度,这片土壤,这片暖阳,连光线都是这个角度,这种感觉难以名状,想哭这就是我曾经熟悉而又陌生的家乡。

篇一:回乡记
星期天,兄弟姐妹一起六个回了趟乡下老家,看望患了尿毒症晚期的二妈。
开车,个把小时的路程,那熟悉的村落渐渐清晰起来。才下过一场雨,临近村子的小道泥泞不堪,乘坐的凯美瑞轿车几次打滑,车身被泥巴糊弄的分不清鼻孔眼睛。好在有惊无险,成功脱离困境了。因为曾经经历过小车陷在泥巴里不得动弹,不得不喊来亲戚八嘎帮忙推车,那悲壮悲催的场景,就像是一坨乌黑乌黑的阴影笼罩在大家伙的心头。
二爷二妈,是我爸爸的弟弟和弟妹。虽然爸爸已经不在了,但是二爷二妈,毕竟是我们最亲的长辈,不能割舍的血缘亲情啊。
二爷身体瘦削,头发花白苍老了很多。二妈更是,走路孱孱弱弱,脸色蜡黄,仿佛冬天里恍惚不定,微弱的没有能量的那一只烛火。
看着真是心里疼痛啊。
二妈一生勤劳节俭,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晚年了却罹患重病。医生说可以做放疗和化疗,以减轻痛苦,延缓生命,儿女们也这样建议支持。二妈却说:“这么大的年纪了,花那个冤枉钱不值得。再说做化疗也是很遭罪的事,人也受不起那个折磨了,不如安安逸逸,过一天算两个半天就行了。”
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想起总觉得还是很残酷。人操劳了一辈子,就这样眼睁睁被病魔夺了生命去?
想我们平时都借口太忙,忽略了她们的存在了。这次,专门给她买了新的衣服,水果,点心,牛奶等,并嘱咐说:“给您一点钱是我们的心意,您不要又舍不得花哟。”
二妈顿时老泪纵横:“我吃的有,穿的有,看见你们了,心里就高兴了·~~~~比吃了喝了还要高兴了~~~~~”叙叙说说老半天,二妈还情不自已,止不住地抬起衣袖揩着脸上皱褶里的眼泪花子。
“哎~~~~~~”我觉得,人生有时候真的只剩下一声叹息了。
回老家一趟,有一些亲戚也是要顺道去拜访一下的。
印象深刻,感触最多的是恩爹恩婆一家。恩婆今年84岁,耳朵背气的厉害,和她说话要凑拢了大声喊着才行。我心想,耳背,或许也是延年益寿最妙的的途径之一?因为,人一生听话太多,受气太多,免不了伤心动怒就折了寿,索性听不见,倒生活的简单快乐!
恩婆的媳妇也是60多岁的人,由于高血压中风,走路踉踉跄跄,似乎总找不到平衡点,一只手使劲挣扎,又感觉有力使不出的样子。一个大约两三岁,光着脚丫的调皮孙子在她膝盖上绕来绕去。
从断断续续的谈话中,我大约听懂了一些故事内容。恩爹,85岁,三个月前死了,死,终是一条遵循自然规律的事情,无可阻挡,但还是让人唏嘘。恩爹在一次码棉梗垛的时候,不小心从垛上摔了下来,遂瘫痪在床。几天后,家人发现,恩爹服了农药,了结了自己的一生(据说是一种喷洒棉花的助壮素,三支即可,瞬间封喉)。众人啧啧感慨说,恩爹一生太造业了,太让人想不得。
恩爹媳妇淡然地讲述,就像是发生在隔壁家的事情。偶尔,不堪忍受孙子的调皮捣蛋和骚扰,就露出极其倦烦的神情,又疼又恼地呵斥着:“自己去玩。”我不禁为这孩子暗捏了一把汗,因为刚就看到屋子旁边有一个长满了水草的大水塘,那水塘可是不讲人情地呢。
话题又关注起恩婆来,恩婆媳妇说:“她现在还好,可以招呼自己,如果哪天动不得了,她也跟自己想好了后路。”大家不可思议地问:“什么后路?难道她不怕死?”
恩婆媳妇也是熬成多年的婆了,可能,晚年的这场中风让她体验到了生不如死,欲罢不能的滋味,于是很了解,很无奈地说:“年纪大了,活着没啥意思了,一代管一代,我们都觉得是娃们的负担了~·~~~”
返程的路上,我大姐(今年55岁)幽幽地说了句:“恩婆80多岁,还有我们这些晚辈们来看她,等我老了,不晓得有没有哪个记得我哟。”
大嫂接话:“肯定有啊,你只怕也会一把鼻涕一把泪,拉着别个的手不放吧?”
二嫂惊醒似的,审视着自己的手说:“好像,恩婆刚把鼻涕弄到我手上了,粘之拉乎好不舒服。”
众人无不狂笑~~~~~~~
篇二:回乡记
父亲年逾古稀,一直想找个机会重返当年下放的地方,也即是我出生之处。条件稍好些,父亲便跟当时的村团支部书记、后来的村支部书记联系上,在镇圩上的路口等着驱车进入。
久未谋面,只是从别处找来的号码联系上。再见面,互相愣怔了半天,打量一番,才喊出彼此的名字。当时的村团支部书记、十七八岁的小伙子早已满头华发,看似与父亲相差无几,精干的个子,幽默爽朗的话语,几句土话,拉回大家熟悉的感觉。
这是乡镇的入口处,需往里走二十几公里才能到达,必须经过三个村子。父亲一路上念叨着这是什么村,那是什么路,沿途有什么变化,那时的树没那么高,现在经过封山育林都长高长密了许多,岔路口那棵大榕树还在,一些老房子依然立着,依稀能看出当时的风貌。路上时不时碰上熟人,老支书不时从车上下来唠会儿嗑,抽支烟。山路崎岖,左拐右弯,上坡下坡,好在都是水泥路,村村通水泥路,交通便捷。越往里走,房子越稀少,树木越茂盛,坡坎也越多,弯道越来越崎岖。摇下车窗,满眼绿意,迎面扑来的是清新纯净的空气,夹杂着山野草木的清香,呼吸变得愈加舒畅,似乎是吸氧一般。车子行驶了三四十分钟,几处大山突兀在视野中,大山围拢怀抱中的村子便是父母魂萦梦牵了几十年的地方——赣南黄坡村。(中国- sanwen.aiisen.com)
这几十年,在父母的口中,这个地名出现的频率很高,但我一直未曾探访过。只是觉得是一个不相干的地方而已。而今真的出现在眼前,首先是觉得此地的特别。它就像是一个世外桃源,据说,除我们进山的水泥路外,还有三条土路四通八达,但需翻山越岭,它在四个乡镇的中心点,因为此地山最高,这片区域便成了真正的世外桃源:宁静、静谧、安逸、祥和。山中野猪、麂子经常出没,据父亲说,当初亲身经历麂子蹿过身边的事。远处山峰郁郁葱葱,树种繁多,尤以山脚下的毛竹居多,绿意盎然,一水的绿色,仿若可以拧出水来的透亮;一条小溪蜿蜒绕村而过,尤能见小鱼儿在游弋。在拥挤的城市群,在工业化的时代,污染源、重金属侵蚀水质日益严重的今天,能看到如此清澈的小溪流真是意外,这是仅存的一些原生态的阵地,退缩在大工业时代的一个角落,如同孩童的眸子那般天真与无邪;田里庄稼已经成熟,黄澄澄的,沉沉地挂坠枝头,一大片一大片的黄寓意着丰收与富足;溪边的果树高大茂盛,恣意地成长,在这,没有束缚,没有憋屈,这是一片沃土,有足够的根基与水分,向人们提供丰硕的果实。
车子开到村头,老支书迫不及待地下来,老支书也离开二十几年了,家中的房屋也早已圮毁,但一年至少回来一次祭祖烧纸。一下车,便碰上村小的校长,当年的村支书之子,也是父亲的学生,认了半天,惊讶地叫了起来,村子平日寂静,少有外人来,在四周劳作的几个妇女,被父母一个个叫出名字来,“代姣”“毛女”“谢姣”眼前的一个个黑瘦、精干的白发妇女从地里、田边、屋内闻讯立即围拢过来,故人相见,分外惊喜,辨认也花了一番工夫,互相打量,毕竟四十多年未见,当年年轻、各有特色的人物谱在眼前呈现,如今已是两鬓染霜、满头华发、面露沟壑、缺牙耳背的老人,这是怎样一种复杂的心境:当年高挑苗条、扯着大嗓门唱山歌的代姣,如今精瘦干瘪黑脸膛,一笑露出金灿灿的假牙,是她吗?当年刚当上新娘、梳着两条大黑亮辫子的、能干利落的谢姣,如今行动蹒跚、体型宽大,是她吗?当年反应敏捷、油嘴滑舌的仪姣,如今不露声色、佝偻着的,是她吗乡音还是那个乡音,只是面容苍老,岁月无情,在四十多年未见的脸上依稀残留着当时的音容笑貌。
大家拉着手走村串巷,在各家逗留,促膝长谈,交谈甚欢,有一种久别的喜悦、激动、兴奋。老支书带我们来到当年生我养我的地方,原来的土坯房屋子早已倾圮不复存在,旁边的屋子残存着当年的木窗,斑斑驳驳,土墙上爬满了南瓜、丝瓜藤,仔细辨认才依稀看得出它的面貌。父亲说,当年我妈在这生我的时候,是他亲自在烧水、伺候,而今当年那个呱呱落地的我,却已成了中年妇人,随夫携子。往右走的正厅门口,七零八落地堆了许多杂物,但两边的门联却依然清晰可辨,隶书体,红字,当年的热血口号“伟大的”父亲一眼认出,这是当年他手书的。
时空凝固在四十多年前,在这个僻静的小山村。
在那个火热的年代,穷乡僻壤里一下涌人了众多外来客。听说此地山清水秀,柴火不用外运,直接上山砍来即可;因为远离乡镇,这安静的一隅可以远离纷争。尽管有些人因路程偏远,交通不便,去了后回来就调整地方了。但父母却依旧无悔地选择这个地方,风景秀美,远离尘嚣。
父母在此待了五年,一个带队管理一些上海知青,一个在村小当教师。父亲当时二十五六岁,说是带队,但与知青们情如一家,在他看来,当时这些上海的孩子们十几岁、二十岁,风华正茂,豆蔻年华,刚从城市中来,闹了不少趣事:不会烧柴,差点把房子烧了;不会煮饭,水放少了,都成锅巴了。父亲也都很照顾他们,有女生不方便时,父亲会安排她们休息,遇有流氓调戏,合力抓起来教训;一起下田插秧,上山砍柴,样样农活,逐渐地熟练起来。当地民风淳朴,村支书和群众也很照顾他们,平时有些番薯、花生农产品都会分些给他们,生活上体贴细致人微,真正打成一片。
知青们在农村,向农民群众学习,体会到农事的不容易,也感受到农民的深情厚谊,水乳交融。直至现在,这班上海知青时常打听老支书等人的联系方式,还时常会回来看望他们,热情有加,一起回味当初那段难忘的经历。而母亲在这个山村里,客家人尊师重教的传统一直没有被当时的争斗所泯灭,对教师都是相当尊重,对文化知识是有着渴求与羡慕的。
当岁月的车轮驶过四十多年,这段经历相信在每个人的生活里都印下不可磨灭的记忆。如火的青春,炽热的情怀,定格在这个门联上。
离开时还太小,才一两岁,但回来时却不觉得陌生,似曾相识。还是这个经度,这个纬度,这片土壤,这片暖阳,连光线都是这个角度,这种感觉难以名状,想哭这就是我曾经熟悉而又陌生的家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