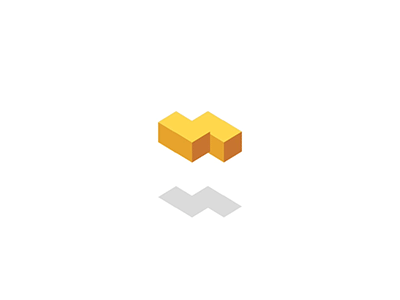从王峰看到侯雪艳的第一眼,他就在想,我得和她搭讪,这是一件必须的事。侯雪艳斯文冷艳,但王峰以为吸引他的绝不是这些,而是,看到侯雪艳他就觉得她是一个同类,就比如在寒冷的南极,一只企鹅终于遇见了另一只企鹅,而不是一只企鹅遇见了一只海豹。广大的人群中,只有他们两个是企鹅,别的都是鱼,虾,螃蟹,或者飞鸟。
王峰在一家机关上班,很多年了从未发生过变化。一毕业就考了公务员,然后在这里的业务窗口上班。每天面对着前来办事的人员,他向他们解释政策,介绍办理的流程。桌子对面的吕晓是一个临时工,每年都考事业单位,但一直没有考中。吕晓的爸爸是一个私营企业的老板,最不缺的是钱,最缺的是吕晓一个稳定的岗位,一个体面的婆家。宁愿一个月不到一千元,老爸也不让她回家,就让她在这呆着。呆着就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就可以在寻找配偶的时候说,吕晓,25岁,本科,人在招商局,家在华林小区,身高一米六五,这些都是天平上的筹码,天平的另一边要有与之等量的筹码,这交易才谈得成。
但吕晓很觉得有颐指气使的必要,每有前来咨询的人员,她都非常不耐烦的语气,似乎唯有如此可以彰显她的高人一等。真是一个肤浅的女孩子,王峰想。其实王峰这么想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吕晓刚来的时候,对老大哥的王峰毕恭毕敬,请教的时候非常甜美谦虚。但是几个月后,当她知道王峰在这里工作十年还不过一个小小的科长,同批进入的早就纷纷升走,她的恭敬已经慢慢的变成了不以为然。尽管她也不怎么流露出来。
每一个来过的临时工,基本都经历过这样一种变化。王峰默默的忍受下去,就像一道红烧鱼的菜,一根刺划过了喉咙,但他没有吐出来,而是咬着牙,在周围的人群中不动声色,悄悄的用力咽下去。划过的地方一定有了细小的血痕,但那是看不到的,看不到,就等于没有。
这么多年,王峰就是学会了使用这种办法来消解他遇到的种种不快。看不见,就当做没有。一个人活在世上,是需要消耗掉种种不快的,你消耗不快的能力,就是你活下去的能力。曾经在妻子离去,一次酒醉又醒来之后,王峰面对着窗外穿过云层的月亮,默默地弄明白了这么一个重大的道理。当时夜色幽深,万物淹没在这幽深的夜色中,唯独天上有淡灰色的光亮,而那光亮的集中处,就是那轮午夜的明月。王峰看着月亮,他感觉种种的痛苦就像此刻的夜空,经过一个漫长而广漠的积郁沉淀,然后逐渐地变轻,变高,变得开阔而旷远。那一刻王峰觉得自己变成了一根透明的羽毛,不停地往上飞升,一直飞升到月亮上去,在那种澄明中融化成了一团。
妻子离家出走意味着婚姻的终结,而这正是当年父母婚姻的复制,只不过当年是男人抛弃了女人,而现在是女人抛弃了自己的男人。失去了父亲的母亲在某一个夜晚投进了镇上的一口枯井中。母亲不是淹死的,是摔死的。不知为什么王峰一想到母亲是摔死的,就立时骨骼之中有碎裂的感觉。似乎假如那不是一口枯井,而是一口水井,假如母亲是淹死的,那么这种碎裂的感觉会减轻好多。
那一年王峰已经上大学了,他喜欢着班里的一个女孩。女孩似乎也喜欢着他。现在想那真是人生最美好的一段经历,彼此有好感而没有挑开,猜测中的甜蜜,向往中的满足。悄悄地买了饭,等在食堂的那个角落,那女孩便也去买了饭,然后坐过来一起吃。王峰想毕业之前多久我向她表达我的爱慕呢?但就在接下来的那个寒假里,王峰经历了与母亲的生离死别。再回到校园的时候,王峰自己都觉得一切都已变化,他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他没有办法再去以从前的心情对待那个女孩。或许就是这种自我的感受散发出去的气息让女孩闻到了,然后没有一个字的说明,慢慢变得疏淡,似乎放假前那种默默而又脉脉的氛围都不过来自臆想。
现在,王峰看到侯雪艳的十分钟已经获得一种信息,侯雪艳像他一样,也是一只来自异地的生物,就如同一只穿过城市的企鹅,注定是匆匆而过的,从身边,从时间里,从空间中流逝而去。
王峰每天回到家里就是他一个人,隔壁是个画画的男子,一脸皱纹,胡子拉碴,从来都没有人来买他的画,他是一个超市商场的保安。他说他曾经开过一次画展,但不管是真的假的,王峰都相信这个叫老韩的画家是一个好人。老韩的家里养着许多鸟,阳台上挂满了鸟笼。这房子据说是老韩的弟弟原来的房子,弟弟一家出国之后,这房子就归老韩看管了。老韩还养了好几只小狗,他看到街上没有人要的流浪狗就领回家来,他和这些流浪狗一起吃饭,他把自己的馒头都撕成小块,扔在菜汤中,那些狗的馒头也扔在另一个盆子里的菜汤中。老韩每天中午回家二十分钟,匆匆忙忙,就是为了回来喂那几条小狗。有时实在忙不过来,就委托王峰替他喂食。
四周邻居们对老韩家的多条野狗普遍地鄙夷加抗议,多次来找,物业的人也来找,说是居民反映和要求的。老韩每一次都喝得两眼发红,脚底轻飘飘的,热情地邀请人家到屋里来,没有一个人肯进去,大家看到老韩的身上沾满了细细的白的黄的黑的狗毛。他们提出抗议,声称这些狗们影响了邻居的生活,老韩就说过几天,过几天找到主人就送走。邻居走了,老韩继续喝酒,压根不提送狗的事,也从来没有打算为狗寻找一个新的主人。他继续若无其事地和那些狗们和睦地生活在一起。
老韩偶尔也翻检出一大堆卷起来、卷成卷的纸,关闭了房门,打开来给王峰看,画上都是画的女人,少女,少妇,中年女人,面目不清而轮廓类似。老韩说那个女人是他的初恋,也是他永生的爱人,刚开头老韩还欲言又止,渐渐滔滔不绝,说这个女人如何地爱他,他们曾经睡过觉,他抱着她沉睡,抚摸她的身体,她的身体光滑而湿润,如一枚水底的生物。“那时候我还年轻,我是一个画家,我的画作发表在中国书画报上,我是全国画协的成员。”有一次老韩的老板因为他醉酒骂了他,老韩回来嘟嘟囔囔地说,将来你死了,连个讣告也没有,我死了,报纸上总要给我发一个讣告的。每次讲到这个,老韩都甚为自许,一丝骄傲从他的眉宇间升起,那个死后的报纸上的一句话对他是如此重要,他用这条没有看到的讣告和他的老板做着精神的较量。
其实老韩是个特别老实的人,后来有次烂醉之后王峰才知道,老韩所爱的女人是他一个近亲的表妹,两个人年轻时候有过一段特别旖旎而纠结的时光,因为家里人
强烈反对,所以结局以悲伤了局。
老韩真的很有绘画的天赋,在他的笔下,三下两下就出现了一只栩栩如生的大鹅,大鹅摇摇摆摆往水里去了;又三下两下出现了一只黄狗,这只狗摇头摆尾,似乎正向着看画的人发出威胁的吠声。
但老韩极少画画,三四年来王峰只看到老韩画过两次画,都是春天,老韩将自己捂了一个冬天的被褥搬运到阳台上去,一一抖开,于是那阳春的光芒水似的扑撒下来,落在那些油污兮兮的铺盖上。在那抹阳光之中老韩眯眼如睡,静静的站上片刻,便如洗了澡一般,眼眉间见到清新的表情,他找出已经快要发霉的画夹,撑在被子后面开始画画。画画时的老韩真有一个艺术家的气象,他的眼睛看不见周边的万物,似乎重新喝醉了酒,一个人在一个不为人知的世界里,微微地笑着,沉浸于一个不为人知的梦境。
也只有在那样的时候王峰相信老韩曾经是个画家,曾经开过一次画展。据说那时他在市物资局上班,业余时间用来画画,画出了一点名堂,很多地方上的人物都来请老韩去画画。那是老韩最为风光的一段时辰,后来这段时辰陪伴了老韩的余生,如同一件值钱的包裹,一个人往前走,总要带着这件包裹前行,因为这件包裹证明了老韩曾经辉煌的过去。
那个表妹后来去向如何老韩没有说过,王峰知道的是老韩有时去楼下的洗发店找小姐,但老韩从来都不承认这个。被王峰遇见从不理发的理发店出来的两次,老韩都说,我本想去理一理发。那样的龌龊事,咱这样的人可不能干。
老韩说当初为了达到结婚的目的,他们向长辈一再表示一生都不生育。近亲结婚的唯一阻碍就是生育的危险。老韩反问说非近亲结婚的人生出来的孩子就一定健康吗?这么问的时候老韩又醉了,他已经有了酒精依赖,只有在喝酒之后老韩才是一个敢说敢爱的老韩。每次酒醒老韩立马变得萧索,如秋风中最后一片蔫头耷脑的枯叶。
老韩和表妹是不敢生育,王峰和前妻却是无能生育。前妻一直怀疑是王峰的问题而王峰一直坚持顺其自然,“该来的总会到来,不来的找也不来”。王峰拒绝去查体的结果坚定了妻子对他没有生育能力的怀疑。一个没有生育的男人就如同一个丧失了阳刚气的男人,失去了基本的性能力、甚至没有阳具的男人。王峰从不这么以为但一直无法抗拒别人这么以为,尤其是无法抗拒妻子这么以为。妻子从未这么表达而王峰却感到这种表达无处不在,在他们家庭生活的每一分每一秒,每一个生活细节之中。
后来老韩的单位效益下滑,直至入不敷出。那时市里的报社社长想请老韩过去,说要开辟一个美术版块,希望老韩能过去主持,老韩很希望能过去,但社长在征求老韩的意见之后,又去找老韩的领导谈时,被领导一口谢绝了。多年以后已经没有人知道领导的目的,大概那时单位马上就要垮掉,领导自己也前途渺茫,他绝不希望手底下的人先行脱离苦海,跳入龙门。就这样老韩的一条眼看着是光明的通途被生生截断了。从此老韩像一条老狗一样趴在那里,再一次失去了所有的希望。
王峰现在想,也许老韩也是一只企鹅,一只衰老的企鹅,一只潦倒不堪的企鹅。老韩自出现以来,就一直这样的颓废,狼狈,每况愈下。他说后来物资局很快解散,弟弟介绍他到一家企业去上班,一开始在办公室,因为喝酒耽误事,便被调到了物业。再后来企业改制,精简人员,所有闲杂人员一律辞退,所以老韩到一家商场应聘做了一个保安。
王峰和老韩成了忘年交,王峰觉得老韩这个人其实是个好人。王峰觉得老韩就是一个更加颓唐的自己。尤其在那曾经的春天,老韩心血来潮拿起画笔来的时候,骤然间散发出一种明亮的东西,这种东西把王峰打动了。所以王峰一直以为,如果全世界的人都看不起老韩,但是他王峰还是对老韩怀揣一种特别的敬意。
王峰是在遇见侯雪艳的第一眼,发生了企鹅的联想。王峰觉得自己是一只企鹅,一只来自南极的企鹅,从一个遥远的地方来到人群之中,城市之中。同时他认准了侯雪艳也是一只企鹅,从另一个空间而来,从南极来到了亚热带,与其他所有的人,所有的生物都是异类。
王峰坚信这一点,他想,我应该和侯雪艳去搭个讪。想到搭讪的时候王峰的大脑中已经想到一个画面,侯雪艳身姿绰约站立在王峰的身边,冬夜的有点凛冽的街道,有点凛冽的路灯光底下,两个人一起漫步往前走,大街上空空荡荡,就只有他们两个人。王峰想这么多年我就是为了遇见她,然后与她走到一起。
王峰想的就这么多,发生一切该发生的事情,并不考虑接下来会怎么样,是相守还是分开,是相爱还是厌恶。爱情到结尾无非这么一回事,不是A,就是B,选择题,没有其他。
只是在这一切之前,似乎都需要一一地预演,比如现在,王峰想的就是我得找一个最最自然的方式,最最合理的借口,跟侯雪艳搭个讪。王峰想我已经老了,在这个世界上我是一个人,没有妻子,没有父母,没有儿女,我什么都没有所以我用不着顾及别人的眼神。上级不可能辞退我,我就是不去他的门前低头,拜会。为了这种坚持王峰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妻子说他固执,同学说他迂,也有人说他轴。但王峰想我只能固执,只能迂,只能轴,这就是我。从母亲被人从枯井里打捞上来的一刻王峰就封闭了和这个世界相妥协的那一扇大门,他关在一个黑暗的屋子里,这间屋子所有的人都看不见,只有王峰一个人躲在里面,他只有躲在这里才有一种放心的安全的感觉,因为这间屋子是所有人都看不见的,所有人都看不见,所以也就所有人都进不去。惟其如此,王峰觉得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一个完全属于自己的地方。
在这里王峰可以一个人都不理睬,不理睬对面的吕晓,不理睬大厅里的任何一个同事,他只和工作的对象交谈,交谈的时候王峰语气平静和蔼,有条不紊,世界似乎是一架精密的机器,每一个链接都是提前设计和操练好的,一起按部就班地往下运行。王峰控制自己控制得很好,非常好,所有人都看不见他有一间独立的小屋他自由地在里面转身和呼吸。因为也没有人注意他,没有注意到,这个办理业务的大厅中来来往往的人,其中有一个王峰,和别人有什么不同。
直到这天侯雪艳到来。王峰所有的期望都寄托在侯雪艳的业务没有办完,王峰要和她搭讪,比如,要她一个联系的方式,比如,邀请她吃一顿饭,或者仅仅去哪里喝一点茶水。
在王峰这么想着侯雪艳的时候他其
实是在设计一场爱情。但王峰从未意识到这一点,更未意识到爱情是可以设计的,他竟然有这么荒唐的想法,设计来的只能是妻子而不是爱人,而妻子已经走了。他在很小很小的少年时代就向往着有朝一日遇见一个女人,就像天空飞过鸟儿雨过了天会晴一样自然的走来一个女人。当他结婚并和妻子生活七年之后他以为妻子绝不是这个女人,也许这个女人永远都不会出现。王峰一点都不焦灼,他把每天的日子都过得按部就班,井井有条,他在一种钟摆一样准确的规律中作息和来去。他经常在一秒钟内爱上一个女人,可是又在下一秒彻底否定了自己的爱情。王峰从来不出去旅游,他是天生要在他现在所出身的一切位置的,他接受这一种安置。王峰朋友不多但还是有几个朋友,王峰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和前妻的关系一样,你愿意来找我,我也愿意,你不愿意,我就接受这不愿意。
侯雪艳穿着一身墨绿色的风衣,她的手指有点粗短,和她的身材不符。侯雪艳的耳垂是那种有点大的耳垂。侯雪艳的眉毛有点稀疏,远山如黛。侯雪艳并不是美,而是一种出神的表情让王峰觉得面熟,他在侯雪艳的脸上看见了一间孤独的小屋,那间小屋如一件行囊,随时背着行走到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就像老韩在某一个春天忽然拿出画笔要打开他的那间小屋晾晒一下一样,让阳光洒落下来,让一切都通通风。
当一间看不见的小屋遇见了另一间,于是在这个亚热带的地域在这个城市一只南极的企鹅遇见了另一只企鹅,如果不主动往前走,那么他们将永远地失去了彼此辨认的机会。
就是怀着这样的紧迫感,在侯雪艳刚刚走出行政大厅的时候王峰已经追了出去。他感到一种失去的焦渴,他本来还在盘算着要等她下一次到来,她的业务还没有完结,她总还要来,但是就在那个墨绿色的风衣穿门而过的时候王峰感到了焦渴和灭绝的危险。一种神秘的力量拉着他从座位上站起来往前奔去,他穿过身边的人群向那个墨绿色的背影追赶,当他赶到玻璃凯旋门的时候侯雪艳已经下完最后一级台阶走到一个站牌的旁边。王峰想快一点,再快一点,否则她就永远地消失不见了,一旦她上了车,她就将彻底消失,永不复现。于是他几乎是抢命一样的前奔,谁知就在他站到离侯雪艳两米的时候,一辆黑色的奥迪Q7停在了侯雪艳的身边。
“侯雪艳。”王峰听到自己的喉咙中喊出了三个字,那三个字飘飘荡荡向前方而去。侯雪艳回头看了王峰一眼,她的脸上带着那间看不见的小屋,随即车门从里面打开。就在她坐进去的时候她问:“是叫我吗?”就在这时车辆已经启动,王峰没有来得及说一句话。街上很多的人很多的车辆,王峰觉得自己如做梦一般,与一个同类的企鹅交臂而过。或许那不是一个同类,而是一只来自南极的鱼,或者其他。
接下来王峰想起老韩那些陈旧的工笔画,或许工笔画的姑娘就是那个从来都不给人理发的理发店里的姑娘,多年之后一切都已发生变化,连老韩自己都不知。也许世界上从来都没有那么一个表妹,一个光滑而湿润的女人,即使有,那个女人也早已在烟火缭绕的生活中老去了,变得面目全非。而这个城市也从来没有什么企鹅,企鹅的幻象是从侯雪艳出现在眼前的那一刻突然出现的,现在也随着她的消失已很快地消失。二〇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12下一页
来源:查字典小小说网 https://sanwen.aiisen.com/xiaoxiaoshuo-17323/更多资源请访问:查字典小小说网 https://sanwen.aiisen.com/xiaoxiaosh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