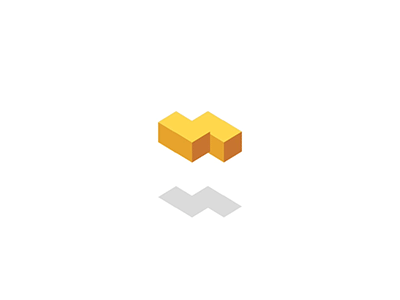+-


地衣吃起来真是清脆爽口,我一生梦想着饕餮大嚼一顿,却始终未能如愿。真正的美食亦属尤物,愈是不可多得,愈是令人牵肠挂肚。
干燥的冬天里,地衣蜷缩在田边路旁的枯草中,一经春雨浸润,便成为柔嫩墨绿的薄膜。所以,在我们家乡,它有一个非常可爱的名字——地软儿。小时候,我常常跟着哥哥去拾地软儿。由于不知地衣究为何物,我曾将一小撮地软儿放在手心,一粒一粒仔细端详。要说它是植物,可是无根,要说它是动物,可又无头。地衣到底是什么啊,又是怎么生长呢?我百思不得其解。于是,跟其他孩子一样,我曾幼稚地以为,地衣由黑乎乎的羊粪蛋儿变化而来。因此,在捡不到太多的地衣时,为了充数,我有时连羊粪蛋儿也捡在一起。等带回家中,父亲看到我拾了半书包,居然比哥哥捡到的还多,便立即打开书包去看。我非常得意,仰起脸等父亲夸奖。“咳!”父亲大喊一声,迅速提起书包,将地衣全抖在地上。我非常吃惊,以为其中夹杂着干草,忙凑过去俯视。不料,父亲却顺手牵羊,揪住我的耳朵,指着地上的地软儿,厉声质问:“你自个儿再看看,这是啥?我把你个坏蛋,竟敢拿羊粪蛋儿充数儿。竟然这么不老实!”哥哥连忙跑过来看,也“扑嗤”一声,转身大笑不止。待父亲松开手后,我一动不动地站着,用手抹眼泪,感到十分委屈。地软儿果真不是羊粪蛋儿变来的吗?那到底是什么啊?一连许多年,我一直想弄清这个问题的答案。后来读书了,才从《辞海》中得知,地衣是真菌和藻类共生的植物,被称为植物界的拓荒先锋。从此,我更加喜欢地衣了。
地衣实在是土地给人的一种馈赠。在那食不果腹的年月里,我最初以为,大人们让我们去拾地衣,跟剜苜蓿、苦菜等野菜一样,是为了充饥。直到有一次,我品尝了一顿地软儿饭,才懂得那是苦难的日子里,穷人们的一种高级享受。按照我们那儿的习俗,每年大年三十除夕夜来临之前,人们按例要吃一顿搅团——一种用玉米面、荞面、莜麦面、豆面或者秫秫(高粱)面在沸水锅中搅成的粘饭。据老人们说,吃搅团的原因是,在年前吃一顿黏黏乎乎的搅团,将心糊住了,一方面辟邪,另一方面好在过年时糊涂涂吃好耍好,啥心也不操。
那年除夕前,母亲说,按照习惯,还得吃一顿搅团。一听又要吃搅团,豆面的豆腥味,秫秫面的粗糙感,一下子让我没了胃口。“我不吃!”仗着是老小,我生气地给母亲丢下这句话,然后拧着头出了屋门。站在院子里,我听到母亲在屋子里喊道:“你个坏蛋不吃!那可不要后悔。”我心里想着,不吃就不吃,留着肚子吃三十晚上的大肉哩。然后,我看到母亲拿出了我年前所拾的地软儿,倒在簸箕里,坐在冬日映照的墙根下,凑近了,一粒一粒地用手指拨着,仔细挑干净其中的细草等杂物,最后放入大瓦盆里浸泡。约莫半个小时后,母亲用清水轻轻搓洗,一边说道:“地软儿这东西,好吃是好吃,可收拾起来麻烦得很。一定放进水里要泡,泡一下,它就展开了,卷在里面的细沙子,才能淘净。尤其是春上让雨淋湿的地软儿,里边的蛆蛆虫虫儿多得很。”最后,母亲将淘洗干净的地软儿盛在竹筛里过水。筛中的地软儿黑中透绿,脆生生的,非常鲜嫩。只要稍微触动一下筛子,它们就会抖动起来,好像又开始生长了。打量着这些,我开始有点后悔了。
我独自一人蹲在后院里,一股股香喷喷的饭菜味儿直入鼻孔。直到哥哥唤我去吃饭的时候,我还在生自己的闷气。哥哥不断催促我,我就是蹲着不动。最后,还是母亲踮着小脚出现了:“谁也没招惹你,看把你牛劲儿大的!”说着,母亲顺手拉起我就走。坐在炕桌旁边,我这才发现今年的搅团不同于往年。往年都是直接搅成的粘饭,今年却变成了汤饭,汤里除了搅团疙瘩外,还有许多猪油渣儿和地软儿。难怪老远都香气扑鼻呢,我暗自思忖着。然后,我假装不情愿地端起碗吃了起来。我注意到,碗中有许多地软儿,油黑油黑地漂在饭汤的表面,铺了厚厚一层。我用筷子拢到一起,慢慢品味。它在口里滑滑的,薄薄的,嫩嫩的,完全来不及咀嚼就被送进了肚子。我原想着要慢腾腾地吃,可吃着吃着,却忘乎所以了,竟一连吃了两碗,直到吃饱之后,才怪自己没能忍住。这时,我才发现全家人都在一旁憋着气偷笑,哥哥用手捂着嘴,最后禁不住大笑起来。父亲斜靠在叠起的被子上,也微微笑着,全没了平日的严肃。
地衣是可口的,然而,我始终未能品出其中的滋味。后来,每年都会尝到母亲所做的含有地软儿的菜汤、包子、饺子等,可是,由于地软儿本不易多拾,太少,只能和在其他食物中来吃。
岁月在积累,久而久之,往往成为重负,压迫我们的身心。我们愈是挺不直身子,我们的理性愈是役使我们挣扎,要从泥土中崛起,乃至脱离土地。我们从土地上匆匆走过,从来不曾想过,地衣无根,却总是贴地而生,是因为它依偎在大地的怀抱,永远不忘大地的恩情。远离土地的日子里,我们的理性常常使我们淡薄了这种恩情,因此,怀念亲人,也常常伴随着痛苦。父母早已离我而去,化作泥土。亲情弥足珍贵,然已不可多得。原来,与亲人们相处,一如地衣贴地而生,当我们远离土地的时候,只能在回忆中重温昔日的幸福。而亲人相处的现实的幸福,也如同地衣,来不及咀嚼,等我们发现它时,就已经远逝了。在我们当初经历它时,和食用地衣一样,是那样地微末寡淡,休味不出其中的真味儿,觉悟不到其中的深情。所以,幸福便常存于回忆之中,使我们在岁月的缝隙里反复咀嚼,回味其真醇。这使我不得不对人类的理性产生了怀疑。
现在,我虽然吃惯了鸡鸭鱼肉,也曾实现了吃一顿生猛海鲜的愿望,可是,始终觉得那些美味儿难以与地软儿相比,因为,它们毕竟是不劳而获的。如同现在时兴的所谓“农家乐”,有些人大老远特地跑到一些偏僻的农村,花钱去享用当年曾吃过一些土特产,想重温其中的生活乐趣,结果却失望而归。
一次,我在网上偶然读到明代王磐撰写的《野菜谱》中与地衣相关的一些文字。王磐描绘了古人拾地衣的情景:“地踏菜(地衣),生雨中,晴日一照郊原空。庄前阿婆呼阿翁,相携儿女去匆匆。须臾采得青满笼,还家饱食忘岁凶。东家懒妇睡正浓。”说凶岁饥民拾地衣“还家饱食”,我觉得多少有点夸张。不过,这夸张原本是为了衬托村民们捡地衣和食地衣的乐趣的。不是吗,那不愁吃穿,正在睡懒觉的“东家少妇”,自然享受不到采拾地衣所带来的生活乐趣。
也许正由于此,我常常忆及童年拾地衣的情景。苍茫沉寂的田野,针针丛棘中的残雪,瑟瑟寒风中的夕阳,疾奔若箭的野兔,这一切的一切,总是牵引着我的思绪,徘徊在旷野上。
最是那冬天里的地衣,若黑色的花朵儿,星星点点,装饰了枯草如被的大地,点缀了关于童年的记忆。而在我们捡拾地衣的时候,得以全身心地关注大地,用我们的手,用我们的眼睛,用我们的心灵。我们会在不经意间触碰大地,意识到地衣与大地的联系是那样紧密,并且在幼稚的心灵里,一次又一次思考着地衣与大地的关系。
地衣紧贴大地而生。只有它,在远离尘嚣的荒野上,在万籁俱寂的深夜里,在尘埃落定的黎明,真切地感受着大地的脉搏,与大地灵魂相依,心心相印,进行着作为万物之灵的人类根本无从知晓的交流。如果不是让人拾起,它将与大地长相厮守。冬天,大雪覆盖的时候,想必它静静地躺在雪下,偎依在大地的怀中,蜷曲着身子,做整整一个冬天的甜梦。春雷滚滚,它们才从梦中惊醒,然后在温馨的春雨中舒展筋骨。
原来,大自然也有美丽的梦。电闪雷鸣,清风细雨,是沉睡之中的大地的梦,梦醒了,大地会重归冷静。我们在捡拾地衣的时候,有幸邂逅了大自然的梦境。那一粒粒、一片片紧贴大地的地软儿,是大地之梦残留在现实里的记忆,尚带着大地的体温,蒸腾着大地的气息。能走进大地之梦,是我们的幸运。拾取大地之梦的遗物,用嘴唇亲吻,大地也将收留我们一度浮躁的心灵,冷却心中的狂热。如此,我们方能同地衣一样,紧挨大地。在我们日渐远离大地的时候,我们的灵魂便漫无目的地游荡,时或放纵轻狂,没有着落。只要重温拾地软儿的日子,心灵便会重归大地,重温那片土地上浓浓的亲情、乡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