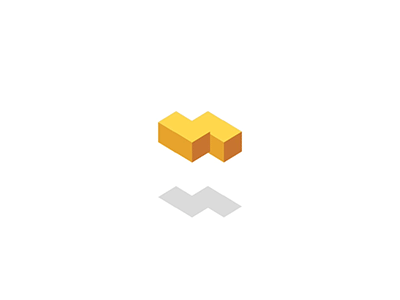这里地处江汉平原腹地,长江最大支流——汉江横贯全境。明朝初年,这里是一片尚未开垦的处女地,境内地势平坦,川泽纵横,土地沃腴,荆棘遍野,荒无人烟。
那时的中国大地,兵连祸结,兵燹蔓延,国民生灵涂炭,饿殍遍野,不少地方人口殆尽,百姓被迫纷纷结伴逃离家园,寻求生计。史上江西几次人口大迁移,多发生在此时期。
在江西先民的大移民潮中,有一对叫周西江 、姚一婷的年轻夫妇,也随移民大军辗转至此,歇脚小憩。他们放眼四望,眼前是一望无垠的湖区淤积滩地。身旁,宽阔清澈的河流,孤鹜点点,鱼摇碧幕;远处,莲叶接天,红幢翠盖,清香四野;脚下,满目闲田旷土,土壤肥沃,土质松软,易于耕种。他们笃定,脚下这块土地就是他们托付余生之地,于是决定不再前行,卜居于此。
很快,他们便劈荆开田,耕种收获。随后,用茅草在河边盖了一间小亭。累了,在亭中歇息;天热时,在亭中乘凉。但凡有人路经此地,亦会在此亭中歇脚。当人问及周氏夫妇此地何名时,回答说不知道,或曰无名。于是便有路人提议:此地只有你们夫妇两,这小亭就借用周西江之名,叫“西江亭”吧,索性此地也叫“西江亭”好了。就这样,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天长日久,“西江亭”的地名身份也就远近皆知了。
之后,陆续有江西移民行经此地,见了草亭,便住脚歇息。他们见田中有一对男女在耕种,遂上前攀谈,方知这对夫妇也是自江西逃难而来,于是便陆续有人随其留了下来。
随之,他们插标占地,初辟草莱,筑园树桑,结庐而居,在这里开始繁衍生息。他们便是我国史上著名的 “江西填湖北”的主角之一。
关于“西江亭”的传说,史海浩淼,无从钩沉,但此地乃赣人迁徙开拓之地已无争议。原来,这里所谓的湖北土著人,其实都是“江西老表”始祖的后裔。
说起“江西老表”这一称呼,长时间来,有着许多传说,颇有争议,人们莫衷一是。后来,学者们力排众议,认定此提法源自于明朝江西大移民时期,与当时一个类似指南针的物件不无关系。相传,赣地先人为便于在迁移途中掌握方向,身边带有一个像表一样的“罗盘”。外省人不知为何物,有见识的人说像一只古老的大钟表。茶余饭后,每当人们议论起江西人大迁移时,总会提及那个像钟表一样的“罗盘”。渐渐的,“罗盘”就传说成了“老表”,后又传为了“江西的老表”。经过长期的谬误流传,便将江西人称为“江西老表”了。
“海内旷土总不如湖广之多,湖广真广哉!”此乃史料对当时湖北广袤地域的记载,有案可稽。明朝时期,湖南、湖北为一省,称之湖广。其优越的自然环境,成为吸纳流移的重要原因之一。
历经近七个世纪,“西江亭”这个地名被一直延用下来。“西江亭”原址如今已成为西江乡政府所在地,这里已发展成一座繁华小镇。当地的老一辈人还曾将这里称“西江亭”,现在的人们通常不再称“西江亭”了,而称“西江”,人们习惯性地将这座小镇称作“西江街”,去镇上称“上街”。而“西江亭”似乎只是特指矗立在小镇街道中心的那一座高大的亭子了。
先民们大迁徙的滚滚尘烟早已沉没,战争的烽火业已熄灭,历史的刀光剑影已然消逝。人们看到的是数百年前江西先人留给后人的时代记忆,飘淌过的凄风烟雨,记录着西江悠久而又厚重的过往。
在那战火纷飞的年月,西江曾有过辉煌的历史,西江儿女为中国革命曾做出过重要贡献。这里曾是革命老苏区,新四军的革命根据地,无数英雄儿女在这里同反动派浴血奋战,数百位革命志士献出了宝贵生命。
如今,西江人传承了先祖们的拓荒精神,在新时代里不断地书写新的传奇。
新中国成立后,血吸虫病在中国大地肆虐,江汉平原腹地也是重灾区。那是一个“千村薜苈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年月。西江儿女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终于打赢了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送走了“瘟神”。今日的西江,早已是“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一派祥和安宁景象。
西江人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使这片沃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现代物流、服装纺织、农产品加工为主的工业体系逐步建全;商业街、商贸大厦、集贸市场一应俱全;以现代农业板块建设、建立新型农民合作社等为推手的建设新农村的步伐不断加快。古老的刀耕火种日月早已转身走远。
今天,我再次踏上这片土地。在家乡日新月异的变化面前,我仿佛感知到了扑面而来的先辈们遗存的浓浓气息。循此,我踱步街头,试图辨认出当年草亭的痕迹。然而,物换星移,沧海已桑田,历经数百载风雨变迁,周氏夫妇的茅草亭已数改容颜。而今,由乡政府出资扩建的“西江亭”,已然是一副钢筋水门汀之躯。
西江亭以一副从容之态,昂然挺立,于四季里,淡看风云变幻,闲览世间万象。高高的亭子,不施粉黛,却风骨依然,如同西江儿女那刚毅的性格和淳朴的品质。那斑驳的印迹,风蚀的黛痕,仿佛在叙说着西江人艰辛的烟火岁月。三层之亭,记载了西江人数百年春种夏锄的过往;六方檐角,挂满了几世纪秋收冬藏的故事。
我站在亭子的檐角下,仰视良久,品味着它那被流光冲洗后的隽永韵致。白日里,亭子如一位老者,饱经世事,吐纳千秋;府览了多少人曾经的迷茫与惆怅,目睹了多少人实现了久远的梦想。夜幕中,亭子似一位妙龄女子,晚风轻拂,霓虹照影,宛如水佩风裳;那挂在亭角的故事在微风中摇荡,好似环佩叮当。这古老而又年轻的亭子,如一首老诗,意境高远,回味深长。
我穿梭在街上的条条小巷。小镇里闾阎繁富,小巷外桑麻翳野。徜徉在这散发着古老气息的土地上,暖阳将我追寻的影子不断拉长。这一刻,我想象着始祖们当年开疆拓土时,曾是怎样的一番筚路蓝缕,才有了今日的沃野千里,物阜年丰,不由心生敬意。值得告慰的是,在这块土地上,我们与祖先有过气息的交汇,有过身影的重叠,也有过梦呓的应和,这是一种血脉的传承。先辈们并未走远,他们的创业精神,正激励后生在这新时代里继续改天换地。
不知不觉,我走出了喧闹的小镇。田间,秋收的人们正在忙碌。我将目光不停地在他们头上扫视,心想,他们戴的可是周西江夫妇曾遗忘的斗笠么?多么想在这秋月春风里,与前人有一次如花在野的邂逅。
我极力地寻找着曾经的西江河,伫足在儿时的河堤旁,眼前幻化出当年的一河清流。河边,见清湾堪钓月,有一叶小舟横。河水还是那样漫不经心地流淌,只顾向前,无意春秋。我来到河边,拾起一支长篙,独上兰舟,优雅地在河中荡漾......然而,西江河的江山早已更改。
我多么想辨认出那条似裙摆飘逸的小河的踪影,去追寻她的足迹,索回那被带走的我的思念、我的青春、我的灵魂。可那一湾碧波去了哪里?
值得欣慰的是,胜利渠还在,她是西江河的姊妹河,虽不及西江河宽阔,河水也不再丰满清莹,但她曾是西江人一条重要的水上交通要道。当年,附近生产队种在刘家湖等地的稻粟,就是通过这条水路运回。站在渠水边,我脑海浮现出了儿时所见的景象:河面上舟楫梭行,河两岸纤声阵阵。我仿佛看到了父兄们那躬身拉纤的身影。当年,我家盖房用的地基石,就是通过这条水路运回。眼下的新农村,道路四通八达,胜利渠也就完成了她的历史使命。她一如一位功勋卓著的老战士,清闲自得,安享晚年。
秋日的下午,走在这熙熙攘攘的人流中,我已分不清自己究竟是匆匆过客,还是眷眷归人。
抬头见一茶肆,便走了进去,在一临街窗边坐了下来。一盏在手,香气氤氲。一抹暖阳孩子般慵懒地趴在茶桌上,暖黄色的,像极了怀旧色,与我此时的心情不期而遇。不由觉得,这小镇里的故事,也被这怀旧的时光所皴染,这小镇岁月的装帧业已泛黄。在这段悠闲的时光里,我温顺地亲昵了故乡秋日里的暖,也缱绻,也缠绵……
暮霭渐沉,亭子显出一种微熏之态,似一抹浓郁的青丹,在这小镇的袅袅烟火里,怎么化也化不开。
我生于斯长于斯,必然有一段前尘往事,自然有一种思念,成为我对这片故土不了的纠缠。每次回乡,都会感到,小镇里的时光柔软得可以疗伤;小镇里的微风婉转得令人沉醉;小镇里的故事多情得足以倾城。
纵然畴昔风云过往,任凭未来世事沧桑,而我与西江将笃守一份地久天长。
早起,我背起行囊,带着先祖们拓荒的故事,带着对未来的期许,向下一个目标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