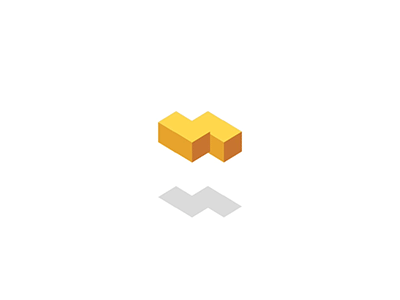父亲一辈子脾气不好,动不动就打骂我们。我们做错了事他打骂我们,他心里不顺时也在我们身上出气。母亲一辈子怕他,弟妹们怕他,当然,我也怕他。小时候我挨打最多,倒不是说我不听话或者老干错事;而是父亲心情不好欲发火时,弟妹们皆躲在了远处,而我则
不躲,像一棵顽强的小树,横在他的面前,任其打,任其出气。
掴一耳光踹一脚的小打可以忽略不计。记得有一次,广场里演样板戏,人山人海的,我们几个伙伴皆个头低,只能看到舞台顶端帷幕的裙边,却看不到台上的人演戏,我们便爬到附近的树上看。我不小心从树上摔落下来,一时间痛得站立不起来,几个伙伴只好搀扶着我
回家。父亲正趴在桌子上写检查。他先不问我伤在哪里?要不要紧?反倒拿起旁边的笤帚把子在我身上狠命地抽打起来;然后又像提溜小鸡似地将我提溜到门外,“哐当”一声把门关上。我流着泪,却不敢哭出声音。那一刻,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我最大的仇人就是父亲了
。第二天,大街上喊声震天,人头攒动。我站在街道旁的台阶上,远远看见几个人,被一伙人反架着胳膊,深压着脖颈,跌撞而来。我分明看见那被押着的人中间有父亲;父亲费力地抬了抬头,似乎也看见了我。在那一刻,我鼻子一酸,却又不由自主地哭了。
高中毕业,大学没考上,我成了待业青年。当时社会上正流行喇叭裤,我也穿了喇叭裤。父亲不让我穿,我偏要穿,他便过来打我。我将他的两只手实实攥住,我当然不可能去打他,但他却打不了我。我们这样扭扯在一起。看着他头上的缕缕白发,额头上的汗珠,颤抖
的双手和气喘吁吁的样子,蓦然间,我感到父亲已经老了,而自己却长大了。我的心像气球似的软了下来,慢慢松开手去,像小时候一样,低下头,任其打。
后来我在临汾钢铁公司参加了工作。我们吃饭需凭饭票。当时,购买饭票有两种方式,一是拿现金买,二是拿面粉换。那年中秋节,正凑得我当班,回不了家,饭票没了,身上的钱也花光了,我两个馒头就着一根大葱过完了节日。第二天,我远远看见有一个人歪斜着身
子,肩膀上扛着什么东西向这边走来,等走近了才看清是父亲。我上班的轧钢分厂离公司门口有八九公里呢。我赶忙帮他卸下面粉。我说,爸,有班车,你咋不坐呢?父亲说他不晓得有班车,他是一路打听着寻过来的。父亲满头的尘埃中夹杂着些许落叶的碎渣,阳光下
油光光的脸,眼角的皱纹里流淌着汗水,肩头的面粉沫子早已被渗出来的热汗糅糊在一起。我两行热泪禁不住扑簌簌地掉落下来,颤抖着嘴唇叫了一声,爸——
那时候,父亲在距县城最偏僻的乔家垣中学当教师,来市里还真是没有几次。
我工作了,父亲打我打得也少了,但叮嘱的却多了。他时常说的一句话是,要努力工作,积极进取,争取早日入党。一个人活着要有信仰;如果没有了信仰就像汽车没有了方向,车翻了都还不晓得问题出在哪里。刚步入社会,尚不谙世事的我,对父亲所说的话并没有去
深入理解。再后来,父亲从教育系统调去检察院工作,我也逐渐成熟起来,并在单位当了中层干部,父亲叮嘱的话也变了。他说,你手中的那点儿权利,往小的说是单位对你的信任,往大的说是人民给的。要始终怀有感恩之心,而不可有非分之想。公家的事情和个人的
事情要分清;分不清就要出问题,一定要秉公做事,清白做人。
其实,父亲并没有太高的觉悟,更没有什么豪言壮语。他做人的原则也很简单:该是他的少一分不行;不该是他的,多一分他也不要。有一次,父亲发了工资,回来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对母亲说,怎么数都觉得这月比上月少了五十块钱,明天我得问问会计。那天晚上
,全家人围在一起看电视。《新闻联播》正播放南方遭水灾,娃娃哭,大人喊,解放军战士大半个身子泡在水里救人。我们倒没啥感觉,偏过头瞟了一眼父亲,微弱的灯光下,看见他的双眸闪着亮亮的泪光。此日中午,父亲下班回来对母亲说,我问会计了,会计说上面
让赈灾,五十块钱单位统一扣了,我又多给了五十,说着将工资递给了母亲。母亲说,为啥多给五十?父亲瞪着眼看了看她,没有言声。瞅着父亲威严的目光,母亲慢慢低下头去,再不敢提此事。
孩子多,母亲时常生病,家里拖累大不说,乡下的那些亲戚总是找上门来,这个说家里要拾掇房子,那个说儿子要结婚,彩礼凑不齐,等等,三百、五百,没多有少,父亲从没有让他们空手回去过。无论怎样,自己总是吃公家饭的,几百块钱掏不出来,谁信?其实,有
时候,家里真的是这月接不上下月了。
当然,父亲也想顺应潮流,搞活经济,以补贴家用,却又没有经济头脑,不懂得市场规律。他见别人家喂猪,就对母亲说,谁谁谁喂了头母猪,生了多少多少猪崽,卖了多少多少钱;谁谁谁喂了一窝母鸡,鸡蛋现在多贵,卖了多少多少钱。然而其结果往往是,等他的猪
生崽了,鸡下蛋了,市场行情却没有了。他在院落的西北角砌了一个猪圈,又让我同他一起赶着老母猪去五里外的配种站配种。我手里拿了木条,深低着头,涨红着脸,扭扭捏捏,生怕遇见同学或什么认识的人。听到父亲在后面说,怎么?没偷没抢的,丢你人了?在那
一刻,我咬着牙,真是恨死他了。
父亲去饲料厂买饲料,买饲料的人多,父亲好不容易排上号,将饲料搭在自行车上一溜烟回来。他掏口袋摸烟,却连着烟摸出一把钱来。他想了想,遂蹬起车子又往饲料厂奔去。饲料厂收钱开票的人早已认识他。便问,老张,怎么又回来了?父亲说,咱们还有事吗?那
人说,有啥事?饲料你不是已经拿上了吗?没事了。父亲再不睬他,放下饲料钱转身离去。
那年,妻子生下女儿刚过周岁。有一日,一个人来我家,拿了一条中华香烟和两瓶汾酒。父亲不在家,母亲拒收,那人强留,两人在院里推推搡搡。母亲怀里抱了孙女,那人又掏出五百块钱塞在孩子手里,不容分说,匆匆离去。父亲下班回来,先是看见窗台上的东西,
又看见孩子正抖动着钱在那里格格地笑。他问母亲是谁?母亲怯怯地说了。没想到父亲竟重重地掴了母亲一记耳光,拿起东西,从孩子手里夺过钱,推起车子便往外走,满院子只留下了母亲和孩子的哭声。
那时候,父亲已经当了经济检察科的科长。在他退休的第二年,经检科改头换面,挂上了反贪局的牌子。
父亲多次荣获过省、市、县优秀检察官荣誉称号。他去世时留给我们的只有三孔已经裂了缝的砖瓦窑、六千元存款、几件早已过时的日用家具和两身崭新的检察官制服。
去年,监察体制改革,反贪局归纪委,各职能单位的纪检组长也归纪委,我是某单位的纪检组长,自然也在其中。作为检察院的子弟,那反贪局长我自然熟识。他开玩笑说,按说,我应当是你爸爸的徒孙呢!我知道父亲当科长时,他经常跟着父亲办案,也经常去我家,
不过只是一般干部。父亲退下来后,由副科长继任,然后才轮到他。于是,我也半开玩笑地说,青山不改,日月轮回。现在你可是我的师傅啊!说完,两人皆呵呵地笑了。实在讲,对检察院我始终有一种个人情结,抑或是缘于父亲的情结吧。看着人家以案说法,逻辑清
晰,思维缜密,我由衷敬佩,暗下决心一定要跟人家好好学学办案本领。然而,就在前些日,我突然得到一个消息,他被市直某执法部门带走了,我惊愕万分,一片迷茫,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我痛心、惋惜,再加上我的检察情结,感到胸口憋闷,竟软软地瘫坐
在那里。
我燃起一根烟慢慢走出机关大楼,看见一辆洒水车正唱着“走进新时代”缓缓而来。雾蒙蒙的水将车前车后的街道分为了两个世界。两旁的花草树木也被冲洗得绿油油的,在太阳下闪着粼粼的光。我抬头望着也像清洗过一般蓝盈盈的天,长长地叹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