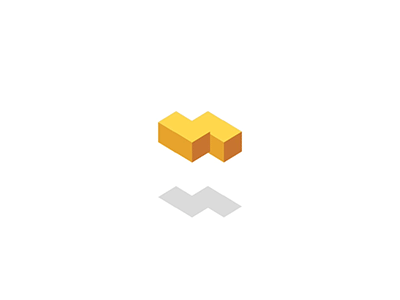著名相声表演艺术家李金斗先生曾经在很多场合说过:北方男人说相声不容易,南方男人说北方男人说的相声也不容易,而南方女人说北方男人说的相声就更不容易。一个女人说了三十多年相声,还是个典型的女人,还是一个把北方相声说得最好的女人,真是太不容易了……
相声名家冯巩先生也曾对中央戏剧学院相声大专班的女徒弟贾玲、宋宁她们说:这个南方女孩子,无疑是当今中国女相声演员的一杆大旗。她给你们提供了很多经典的范本,她也给很多想说相声的女孩子树立了标杆,她在作品和表演当中传递出的真善美,值得每一个女孩子学习。
天津市艺术研究所原所长、已故著名相声理论家刘梓玉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应该说,这个女孩子的出现,是中国相声队伍的一种幸运。她就像一支小夜曲,宁静中传出幽默的旋律、柔和的音符,给千家万户带来了欢乐。
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朗昆先生撰文说:2003年,她和她老公倪明带着一段令人耳目一新的相声《永远是朋友》参加了春节晚会的节目竞选,当时被媒体称为“春晚的一匹黑马”。尽管最终没能亮相,但给我的感觉是:妇唱夫随、名不虚传。
中国曲协著名曲艺评论家黄群说过:她的人生就像是一次旅行,相声是她这次旅行当中不可或缺的欢乐,而她也是播撒欢乐的人。别人欢乐,她更欢乐。
中国艺术研究院曲艺理论家蒋慧明说:在枝繁叶茂的相声园地里,她是辛勤耕耘的小蜜蜂,拥抱花香、吻着甜蜜、散发笑意、播撒美趣,她的执着、探索、传承、创新,让她显得独树一帜、与众不同。
……
以上这些名家大蔓所描述的这个女人不是外人,就是集我的夫人、太太、爱人、老婆、婆娘、俺家的、孩子他妈为一体的——夏文兰。
江湖人称“中国相声一枝花”“江南笑坛女才子”。
文兰从记事那时开始,绝对不会想到能和中国的相声结缘,可是自我接触她的第一个“包袱”起,就认准她是干这行的材料。所谓人的命,天注定,恐怕就是这个道理。
那是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夜晚,文兰年轻力壮的父亲因为工期完成得好,拿了一笔奖金,就和工友们大块吃肉、大口喝酒,这一喝就是二斤多,好在那时候没什么假酒,要不然肯定危险。但二斤多白酒对于一个不常喝酒的人来说已经是大大地超过极限了,这一喝就到医院抢救了。当着全家人的面,大夫指着文兰的爸爸说:不行了,不行了,赶紧回家吧!
全家人吓一跳:怎么了?大夫?
大夫扒开文兰爸爸的眼睛说:看见了吗?眼球都不动了,赶紧回家吧!
这时候文兰说了一句话,大伙全乐了:大夫,我爸爸有一只假眼……
这个颇有点相声泰斗马三立特点的笑话,却是文兰一段真实的生活。当她在天津见到马三立先生本人时,还不忘“调侃”一句:您老人家相声里说的就是我爸爸。
文兰和我都出生在黄海之滨的苏北盐城。
盐城,是新四军重建军部所在地,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刘少奇、陈毅都在这里工作过。所谓 “陕北有个延安、苏北有个盐城”就是这么来的。
盐城,以产盐而盛名,以淮腔而享誉!
它地处江苏沿海中部,东临黄海,南接南通,西与泰州、淮安接壤,北与连云港隔河相望。盐城的地域文化在历史上属于楚汉文化与淮扬文化过渡带,因战乱及人口迁徙等因素,又受到吴文化、江海文化的影响,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资源,又让它形成了具有“浓郁咸卤味”的独特海盐文化。
盐城境内有平坦的滩涂、广阔的水域、纵横的沟渎和茂盛的芦苇柴荡,具备海盐生产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作为全国唯一一座因盐命名的城市,盐城因盐而置又因盐兴盛。“煮海为盐”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炎帝时期,周代已有先民来此搭灶煮盐。《史记》称“东楚有海盐之饶”,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建立盐渎县,东晋命名为“盐城”。唐代成为东南沿海重要产盐中心,“天下之利,盐利居半”。宋代在盐城设盐仓。明清两代,盐场大兴,徽商以盐利竞豪富,淮扬之繁华锦绣颇多源于盐城。至今,盐城仍是中国重要的海盐生产基地之一。
北宋三代名相晏殊、吕夷简、范仲淹先后在此地任盐官,范仲淹带领通泰楚海数万民众筑堤防潮,留下名垂千古的范公堤。南宋海国孤忠陆秀夫负帝蹈海,以身殉国,永垂青史。元末张士诚率盐民起义,一度据苏州称王,与朱元璋争雄天下。革命战争年代,刘少奇、陈毅等老一辈革命家率领新四军在此浴血奋战。当代既有“党内一支笔”胡乔木,也有杰出外交家乔冠华。至于周巍峙、曹文轩、吴为山等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白头灶户低草房,六月煎盐烈火旁。走出门前炎日里,偷闲一刻是乘凉。”明末清初著名盐民诗人吴嘉纪的这一首《绝句》,是对盐城文化内涵特征的诗意写照。恶劣的生存条件和长期的艰苦劳作,培育了盐城人民刚勇坚毅、奋发进取的主体意识;残酷的自然灾害和频仍的战乱匪祸,练就了他们不畏强暴、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团结互助、团队协作的生产方式,练就了他们团结拼搏、艰苦创业的团队作风。历史上在此诞生的新四军“铁军精神”和今日盐城倡导的城市人文精神,与海盐文化一脉相承。
在我的记忆中,盐城好像没有什么属于自己的曲艺形式,即便后来比较成熟的盐城方言快板,也是在吸收了传统地方戏和北方曲艺元素的基础上而建立起来的。至于像什么道情、渔鼓、表演唱等早就难寻踪迹了。
我接触曲艺源于我的父亲。他老人家天生乐观,一辈子在水上搞运输工作,注定心胸非常开阔、乐观豁达。老爷子闯荡江湖的经历简直就是一本天书。天下之事,无所不晓。就像马云所说:一个人的见识远比他的知识、学识来得重要。
说起来非常有意思,就在老爷子八十大寿的时候,我请他到南京散散心,早上一起下楼买菜,刚走到路边,突然来了辆电瓶车,不小心碰了老爷子一下,老爷子也没当回事,可当我问他:有事吗?
他立刻捂着肚子“唉哟唉哟”地喊起疼来。
我说:别唉哟了,人家已经走远了。
他立马起身乐呵呵地说:没事!
我笑着对他说:我这辈子不说相声都对不起您,您比我在台上的表演还精彩。
他也笑着回答我:这回知道碰瓷是怎么来的了吧?
我记事的时候,已经六岁多了,那时候正好赶上“上山下乡”的运动,我妈又是居民小组长,所以要带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可怜我的老母亲,带着我们兄妹五个在农村一待就是十年。
这十年,也是我母亲吃苦受累的十年,是饱尝人间冷暖的十年,也是我们兄妹几个不断成长的十年。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全家冒着大雨,坐着一条机帆船,经过几个小时的水路来到了下放地点古河村。听说要到农村去生活,当时年少无知的我们还兴高采烈,可是搬家上了岸,全家人就都傻了,这哪是人住的地方啊!外边一间屋养着三头牛,臭气熏天,里面铺着稻草的地方就是我们全家六口人待的地方了。要出门必须先绕开那三头牛,一不小心还会踩上满脚的牛粪。我们下乡时的高兴劲很快就荡然无存,心底突然产生一种莫名的悲伤。
最可怜的是我母亲,从来没干过一天农活的她,居然每天要下地割麦、插秧、挑粪、浇地、耕田、脱粒、挖河、引水。凡是农民干的活,我母亲没用多长时间就全都学会了。不学会也不行,因为那时候按工分算,不下地干活,全家人就得挨饿。我父亲那时候也不太平,被关在学习班里整天挨批,每月往家里寄五块钱,就这五块钱,成了我们全家的救命钱。
都说穷人的孩子早当家,我也不例外。看着母亲和哥哥姐姐们吃苦受累,我从小就学会了做家务活,家里头什么时候都是干干净净的。一到生产队要开会,队长准通知到我们家里来,不光环境干净,我还会给他们沏茶倒水。
也就在这十年当中,我成了农村小学宣传队的骨干,但凡有演出,老师必定安排我唱歌跳舞带报幕。记得小学二年级的时候,老师组织我们到古河村的打麦场上演出,我上场一跳,台下就掌声笑声不断,有的大妈还边指我边乐,我以为大家特别喜欢我呢,没承想,女班主任笑着捂着肚子对我说:下次跳舞别穿开裆裤了。合着人家乐的是这个。
由于我在家里排行最小,所以,每到寒暑假我总能优先跟着我父亲出去旅游,其实就是坐船从盐城到镇江一带。要知道,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交通非常不便,最好的交通工具就是坐船,上到政府官员,下到平头百姓,全都一样。就在来来往往的旅途中,我认识了一位卖唱的民间艺人,他姓曾,原来是专业剧团唱戏的,后来“倒仓”(嗓子坏了),加上婚姻不幸,他干脆下海跑起了江湖。平常在船舱里帮游客递茶倒水、送饭送面,一有闲空,他就在船舱里卖起小唱。当然唱的全是传统戏,我也就在那个时候,知道了什么是《河塘搬兵》,哪个是《杨门女将》,包括《探寒窑》《珍珠塔》什么的。最让我感兴趣的是,曾老师还能说一口流利的方言快板,是夹在扬州和淮安方言之间的那种,说完之后,居然还能收到一毛、两毛、五毛和很多硬币。这玩意儿还能挣钱?这对我的刺激那可是太大了。于是,我也模仿着他给大家表演,居然也收了个三毛五毛还有很多吃的上来。这不就是当年相声的撂地卖艺吗?
我后来在舞台上经常表演的快板《有口难言》,就是根据曾老师的《还是一个好》改编的。包括在盐城一带一直很火的快板小段《卖花生》,都有曾老师的影子。直到后来一个叫王红专的出现了,我觉得他表演的方言快板比我地道、有味儿,就主动让出了这两段比较经典的作品,也成就了后来成为苏北快板大王的王红专,这是后话,另有表述。
如果从曲艺拜师收徒这个角度来看,这位跑江湖的曾老师应该算我的第一位启蒙老师,尽管后来我再也没见过他。也曾经托人四处打听,但最终还是没见到。传说他早已经离世了。因为他特别的贪酒,身边又无人照应,结果不容乐观似乎是注定的。但他无疑对我的兴趣爱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所以说,童年的教育环境太重要了,所谓的“跟好人学好人,跟着唱戏的学戏文”,就是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