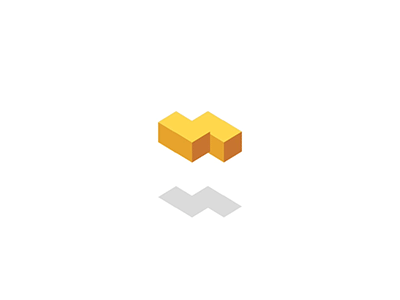《酱豆》比《暂坐》的草稿早,《暂坐》却先在刊物上亮相,“早知灯是火,饭熟已多时”,《暂坐》走的是电影节大厅前的红地毯,《酱豆》从后门悄然去了会堂。
之前我所有的长篇小说写作,桌上都有收集来的一大堆材料,或长之短之提纲类的东西。而《酱豆》没有,根本不需要,一切都自带了,提起笔人呀事呀,情节场面就在眼前动,照着写就是了。而之前写完了长篇小说也全有后记,《酱豆》还是没有,因为要说的话正文里都说了,甚至当初给它起名时就是《后记》。
《酱豆》的修改誊抄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每顿抓一把米做干饭或稀粥,菜已经很少,一日三次的连花清瘟胶囊必须保证,三个月的自我隔离,外边世界有毒,我也有着,把它写出来了,就是一场排毒。
我在题记上写:“写我的小说,我越是真实,小说越是虚构。”《酱豆》的故事,无一事没有出处,但人物有归纳,时间已错落,还有那些明的暗的,清晰的含糊的,不是卖弄和兜售什么,为的是一直要拷问自己。我这近七十年里,可以说曾经沧海,比如生于共产党军队的团部,团部又驻在大地主的庄院;比如少年时期的土改,反右,公社化,社教,“文化大革命”,回乡知青,反革命家庭可教子女;比如青壮年间的工农兵上大学,计划生育,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反自由化,清除精神污染;比如再后来的干旱,水涝,地震,瘟疫,病疴沉沉,城市化,金融危机,反腐,扶贫。每一个历史节点,我都见识过和经历过,既看着别人陷入其中的热闹,又自己陷入其中被看热闹。
我曾在很长时间里疑惑我是属于知识分子之列吗?如果不是,那么多的知识分子的遭际和行状,应该让我如何读懂中国的历史和历史上的那些仁人先贤?如果还算是,我是在什么位置,又充当的哪一类角色?每一次我都讨厌着我不是战士,懦弱、彷徨、慌张、愧疚、隐忍,但我一次又一次安慰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写作呀。曾感叹如袁宏道的法“衣败絮行荆棘中,步步牵挂”,又曾迷茫如一漫画中的题“当斧头来到树林里,好多树却说,至少它的把手是我们自己人”。我是太热爱写作了,如鬼附体,如渴饮鸩。一方面为写作受苦受挫受毁,一方面又以排泄苦楚、惊恐、委屈而写作着,如此循环,沉之浮之。时至今日,想之,这或许是命,再想之,初入文坛写过的《丑石》那么受到误解,写过的《一棵小桃树》又是那么风来压在地,风过再浮起,都是谶语啊。
哦哦,已经这把年纪,还能写就继续写,最想写些啥就写些啥,苟做,苟做,长吁成风,呵气为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