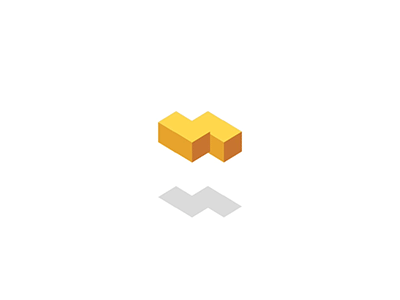读完郑振铎的《蝉与纺织娘》,倘若你能再找来法国科学家法布尔的《昆虫记》,看一看里边的那篇《蝉》,那么你一定会产生莫大的兴趣,发现存在于这二者之间的微妙的差异。
的确,《蝉与纺织娘》不同于郑振铎另外一些散文,这里没有激越的基调,没有愤怒的抗议,只是记载了自己对大自然中虫鸣之声的细致观察和自己的一次独特的经验。从这点上看,与法布尔的《蝉》实在没有什么区别。《蝉》的开头是这样的:
“我有很好的环境可以研究蝉的习性。一到七月初,蝉就占据了我门前的树。我是屋里的主人,它却是门外的统治者。有了它的统治,无论怎样总是不很安静的。”
在极精确、生动地描写了蝉的习性和生长史以后,法布尔这样结尾:
“四年黑暗中的苦工,一个月阳光下的享乐,这就是蝉的生活。我们不应当讨厌它那喧嚣的歌声,因为它掘土四年,现在才能够穿起漂亮的衣服,长起可与飞鸟匹敌的翅膀,沐浴在温暖的阳光中。什么样的钹声能响亮到足以歌颂它那得来不易的刹那欢愉呢?”
但是你再读几遍就会发现法布尔的语言于生动有趣之外,更在乎精确、细密。他记录了蝉孔的口径,他描绘了蝉的幼虫脱皮的全过程,他探究着蝉在地下生活的秘密。而郑振铎的语言于淡朴清新以外,更注重主体的内在情绪,宛如一首抒情诗。那时常出现的排比句与博喻荡漾着深沉的历史感,或充满生机,或徘徊着淡淡的哀愁。“洞箫”,“红楼重幔”,“秋风落叶”,“怨妇”,“琵琶”,“荧荧油灯”与“迎风而唱”,“生之歌”,“生之盛年之歌”,“结婚歌”形成了鲜明的两极。
法布尔对蝉的习性的记录有根有据,给人一种实实在在的感觉; 郑振铎在文中记录的那次独特经历——听到了纺织娘的歌声之后再听到蝉之夏曲——则让人回味无穷: 兴许这确是自然界的一次偶然事件,兴许这只是作者的一次主观失误? 但追究它的可靠性又显得毫无必要。因为从根本上说,《蝉》的对象是自然,《蝉与纺织娘》的对象是人化自然。
这是如此地有意味,我们可以想见法布尔是怎样蹲在地上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自然而洋洋自得;而郑振铎则是躺在沙发上,喷着烟云,用心灵的眼睛去看,用心灵的耳朵去听,并怡然自得地陶醉于其中。所以,这就叫一为科学家,一为文学家;一为科学小品,一为散文。
这究竟是民族的不同呢,还是个人好恶的差异我们说不清楚。法布尔认为有了蝉声总是不得安宁,只是在细叙了蝉的生命之艰难以后才颂扬起蝉来。而郑振铎则能在蝉声中安然入睡,并获致一种清凉的感受。但有一点却是可以肯定的,法布尔的注意力始终在蝉身上,而郑振铎的目的则最终在要转移视线,要让对蝉声高旷之音的赞美,对独特经验的诗意描述,引领出一种精神,一种只属于人的、蓬勃旺盛的、生生不息的精神。从这个意义上说,郑振铎“为人生”的创作主张又一次得到了曝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