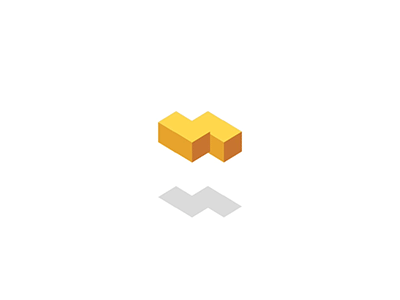在湖北的革命老区水湖,父亲本有一处老屋,后来因为进城养老卖给了同村的乡亲,很长时间没有回去看看了。2018年的一个秋日,已是92岁高龄的父亲提出回去看看老屋,我便驾车陪他前往。
汽车在水湖的原野上行驶,但见村落安静祥和,庄稼收获在望,我们很快来到古汉堤东的一处农舍,这里碧水荡漾着乡愁,绿树掩隐着根脉。下车后,我要扶父亲上台子,他却执意要自己爬上那20级台阶。一个九十二岁的老人走向自己阔别多年的老屋时,虽然有些颤巍巍的,但却显得格外精神。房主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并领着父亲来到前院大门。老屋敞开大门笑迎这位曾经的主人,而父亲则眯缝着双眼对老屋仔细端详,他们象两位阔别多年终于重逢的好友,久久对视。父亲的脸上带着微微的笑意,眼里含着晶莹的泪光,与老屋沉浸在一种自然的交流中,默默地回味着属于他们的过往——
父亲原有一处不错的祖屋,但六十年代初,叔叔带着漂亮的婶婶从天门精简回乡后,父亲便把祖屋给了他们,自己在低矮的台基上搭了三间草房,开始了一家人的“新生活”,也正因此,让自家有一处漂亮的瓦房成了父亲人生的梦想。
水湖多水,每当汉水上涨,多有溃堤之虞,所以生活在水湖的人们总把自己的房基筑得高高的。面对洪水的威胁,父亲发誓要用自己的肩膀为妻儿挑起一个安全的台基,从此在他的日常劳作里又多了一项任务。多少个清晨,当儿女还在梦乡时,他就和母亲出发了,母亲挖土,父亲挑土,他迎着霞光,哼着小曲,一筺筐担起,一程程往返,汗水一次次打湿他的衣衫,母亲帮他擦擦汗让他歇歇,他总是说不累。多少个夜晚,忙了一天农活的父亲又挑起箩筐,星光里扁担吱吱作响,和着脚步的踢踏声,奏响父亲对未来的向往。那几年,春花的清香里绽放着父亲的心愿,夏雨的淅沥中冲洗着父亲的汗水,秋光的潋滟里映照着父亲的身影,冬雪的妙曼中烙印着父亲的脚步。这样的坚持,浇筑起一个十米多高、120平方的台基。完工的那些天,父亲心里乐滋滋的,只要有时间,他就到台基上这儿走走,那儿看看,这里踩踩,那里锤锤,就像一位作家在反复修改自己的作品,不肯错过一个标点符号。
台子筑起后,父亲便思谋着盖新房。没有砖,父亲就自己先做土胚,再借小队的土窑烧制;没有瓦,父亲就到小队机瓦厂帮工,换取低价购买;没有木料,父亲到东山去打工,挣钱买回。父亲靠着自己的双手把一切准备妥当,便开始建房“工程”。下脚那天,他放了整整几挂长鞭,领着帮忙的乡亲打夯,他领夯的号子是那么嘹亮,仿佛把一生的追求都唱了出来。一个多月后一个四合小院便建成了。这是一个极具乡土特色的水湖派建筑,一主两厢,青砖灰瓦,周正庄重,简朴实用。正房是三开间大房,坐西朝东,中间是堂屋,南北是居室;厢房均为两开间,配有仓廪和厨房,中间是一个天庭,前有围墙大门。新房落成那天,父亲喝得酩酊大醉,因为这是他一辈子最大的事业,就像一个画家画出了一幅惊世好画,他有理由陶醉。
这个极为平凡的农舍,在水湖的风雨剥蚀中屹立了四十多年。它是父亲用担当筑起的丰碑,用慈爱编制的摇篮,用深情凝成的守望。这里的相聚与分离,交织出苦涩年代艰辛而温情的记忆。在这里,他和母亲养育了两双儿女和两个孙子。在这里,他为老大成家立业,含饴弄孙;他为老二置办嫁妆,送其远嫁;他陪老三秉烛苦读,挤上高考独木桥;他教老幺学习会计业务,外出闯世界。多年后,老屋已经有些老旧,但正是这种老旧沉淀着家庭的历史,凝聚着亲人的情感。
2000年,父亲年届77岁,身体日渐衰老,我们决定把父母接到城里养老并把老屋卖掉,父亲坚决不同意,说死也要死在这里。但后来因母亲的一跤摔得很重,需要有人照料,父亲不得不妥协。当年国庆假期,我们兄妹一起去接他们,当一切处理完毕,却不见了父亲,后来发现他把自己关在里屋久久不愿出来,透过窗户,我看到父亲正在抚摸他的桌子、椅子、柜子还有白墙,一边摸家什一边抹眼泪……
不知在大门前停留了多长时间,父亲终于挪动了脚步。房主牵着父亲,陪他看房间,看果园,看竹林……他看到,他亲手做的砖瓦依然青灰如故,他亲手种的柑橘已经硕果累累,他亲手植的竹林已经长满后院……他笑了,笑得像个孩子。然后来到一棵遒劲挺拔的杉树下,他用双手箍抱这棵有着40多年树龄的老树,轻轻地摇着,嘴里喃喃道:我当年栽你时只有拇指粗,现在却有水桶粗了。树上有叶应声落下,纷纷扬扬,父亲赶忙用手接着,捧在胸口,倚着老树对着老屋深深地鞠躬。他又拉着房主的手久久不愿松开,不断地说谢谢!之后他几乎是一步一回头地离开了老屋。
汽车驶离老屋,行到老铁业社时,父亲突然叫停车。下车后,隔着雪花如海的棉田,父亲再一次对着他的老屋久久凝视,眼神定定的,显得那么深沉而专注。夕阳在霞光的簇拥下,透过树叶暖洋洋地洒在地面,空气显得格外清新,西边的老屋也涂上了一层金黄。柳枝在微风中摇曳,轻拂着父亲的脸,突然父亲摘下鸭舌帽,向老屋挥动着,不住地挥动着……
这是一幅令我感恩而刻入骨髓的画面,里面有秋高气爽的黄昏,更有父亲慈祥而清瘦的背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