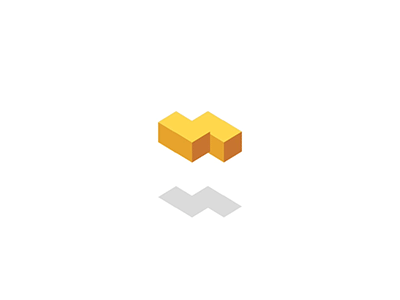+-


几天不见,父亲好像又老了许多。佝偻的身体,左肩像压着一块石头,深深地塌陷下去。倾斜弯曲的身体,踯躅而行。布满血丝的浑浊的眼睛里,写满了忧伤。脸上石雕般的皱纹,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再也找不到昔日里那容光焕发、健步如飞的影子。父亲是老了,已经八十七岁了,在我们那,是实实在在的“老寿星”。
清晨,霞光洒满了天空。父亲的庭院里,高大的杏树,郁郁葱葱。院子中间,有几块大石头,上面零散地摆放着几盆鲜花。花朵上挂着露珠,在朝阳的映衬下,娇艳欲滴,姹紫嫣红。庭院是简单的四合院,五间瓦房坐北朝南,东西两侧是两间厢房,南边是厨房、猪圈、羊圈、厕所等。猪圈、羊圈里空荡荡的,也听不到鸡犬相闻。微风吹过,几片树叶簌簌地落下。
父亲从睡梦中醒来,浑身一阵酸痛,努力地抻抻又酸又胀的腿脚。肿胀的右脚将鞋子撑得满满的,“咦,吃得好了,脚还在长呢”,父亲暗自纳闷。父亲把几个水缸灌满,并把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照例,今天是赶集的日子,自前几天父亲摔了一跤以后,脑袋昏昏沉沉的,腿脚更不灵活了。父亲摇了摇头,放弃了赶集的计划。已经错过两个集市了,父亲倍感遗憾。
在商贸不发达的农村,农贸市场(集市)显得尤为重要。赶集依旧是农村的头等大事。到集市上买些新鲜的瓜果蔬菜、种子菜苗,买些日常的生活必需品,足以用到下一个集市前(五天一集)。那些养牲口的、种菜的都早早地来到集市上,希望能卖个好价钱。以前,父亲逢集必赶,而且,去得很早,赶集的人大都认识他,对他礼貌地打招呼。父亲笑语盈盈,挨个询问市场行情。我堂哥曾打趣地说,“叔,你若不到,集市不能开市啊”。其实,父亲赶集,买的东西非常有限,无非几斤水果,几个烧饼,偶尔买点秧苗和种子。父亲赶集,就是图个热闹,看熙熙攘攘的人群,听高声的叫卖声,欣赏琳琅满目的商品——集市上,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充满了生活气息。
父亲的正房,也叫堂屋,迎门摆放着一张长方形的供桌,桌子周边雕刻着精美的花纹,黑红的油漆已斑驳陆离,变成了灰白色。桌子两侧是一对圈椅。墙上暗红色的古老的挂钟,依旧在悠然地摆动。大大的“福”字,寄托着人们对幸福生活的希望。桌子上,父亲巨大的照片格外醒目:父亲佝偻着身体,身穿灰蓝色的上衣,胸前挂着金灿灿的“在党50周年”纪念章,眉眼嘴角都堆满了笑意。照片前,是一个红色锦盒,“在党50周年纪念”几个大字耀眼夺目。锦盒里,红色绸带下,悬挂着沉甸甸的纪念章。奖章金光灿烂,熠熠生辉。
本村荣获纪念章的只有七个人,党龄足够长才行。父亲感到无比的光荣、自豪和深深的归属感,将纪念章摆放在最显眼的地方。来人便炫耀一番:“你见过这东西吗?”来人摇摇头,展示过后,父亲便说:“这可是金子的吧?”“好像是,值不少钱哩”。父亲得意地笑了,“咱村里只有七个人才有”,人家便迎合着,说道:“是啊,都是给国家做过贡献的,国家没忘了你们啊!”有一天,父亲不无遗憾地对弟弟说,“这金牌能卖不少钱,我死了,可没法花了。”弟弟也不生气,笑着怼他:“等你百年之后,会把它放到棺材里,一起埋了。”父亲满意地点点头,略加思索,依旧不放心,“不行,万一让盗墓的给扒走了呢.......喔,现在已经没有盗墓的了。”
得到纪念章至今,已两月有余,父亲依旧将纪念章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锦盒上布满了一层薄薄的灰尘,但心底的那份荣耀、自豪依旧在暗流涌动。
时光流转,人们对那个金灿灿的纪念章早已淡忘,走在路上也无人问津了。摆在桌上的锦盒定格成了雕像,来观看的人越来越少,热闹的庭院也恢复了往日的寂静。心底升腾起的荣耀和自豪,像一个个绚丽的肥皂泡,瞬间破裂了。父亲感到无限的孤寂和失落,喃喃地说:“都不喜欢老头老太太,可是国家喜欢。一个月给330元,吃什么也吃不完啊!.....这个社会是真好,历朝历代也没有现在的年代好。”我故意问道:“好在哪里呢?”“不交皇粮,还给老人发钱。我一天坐着不动,都有11元钱!哪有这样的好事?!”果然,知足和感恩是幸福的源泉。父亲从不抱怨社会,对党和社会充满了感激。但父亲不知道的是,现在的物价已经与五分钱一份大锅菜的年代不能同日而语了。前一阵,弟弟给父亲做个全面检查,便花掉近四千元。
父亲一生勤俭,惜时如金。在父亲的眼里,总有干不完的活:晴天下地除草,雨天搓麻线、编柳筐;清晨浇菜园,傍晚挑水和清扫猪圈。父亲把里里外外打理得井井有条,从不舍得睡一个午觉。现在,父亲不能到农田耕种了,只在院门外开辟了一块菜田,种些时令蔬菜。
“人生一世,草木一秋”,树叶也有飘零的时候。几十年间,父亲送走了一个又一个亲人:我奶奶、母亲、姑姑、姑父、大爷、大娘......同龄的伙伴们也先后离他而去,孤独、悲凉和惶恐写在脸上。“唉,快轮到我了”,父亲一声哀叹,“我倒也不怕死,多活了二十年了,也该知足了。就是临死前的遭罪......我没伤过天理......”明白父亲的意思,他认为没干过伤天害理的事,应该不会遭受很多痛苦。父亲就这样自言自语地说着,我搭不上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能静静地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