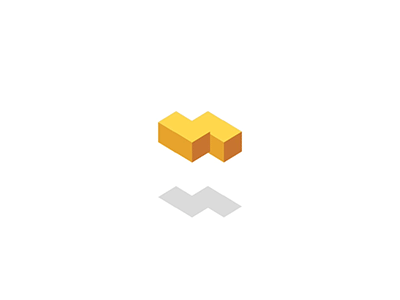(税月牛痕)
公元一千九百五十八年,以“大跃进”为主要印记的“三面红旗”运动,席卷了整个中国。全国5亿多农民,为了适应“组织军事化,行动战斗化,生活集体化”的要求,被迫放弃了世代相传的以家庭为单元的生活方式,携家带口地走进了公社、大队、生产队为他们兴办的“公共食堂”,过起了现代“乌托邦”式的生活。笔者当时是一名小学生,作为一个普通农民的后代,亲历了这段荒唐事件的全过程。
10天时间正式“开伙”
改变人们数千年生活习惯的变革,在“一天等于20年”的狂热年代,过程竟变得异乎寻常的简单。
58年8月上中旬,报纸上首次出现了河南建成人民公社的报道。随之毛主席向全国发出了“人民公社好”的著名号召。被经年累月的“整风反右”运动搞得人人自危的各级干部,在主席的号召面前,响应唯恐嫌迟,没有谁敢对这个问题表现出半点的怀疑与懈怠。58年8月30日,中共淮阴地委向全区发出了《关于大办人民公社的意见》,之后,全区仅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即于9月13日宣布全部实现公社化。全区12个县共成立259个公社和12个国营农场。入社农户达1210548户,占总农户数的97。6%。270多个公社(农场),又以生产队为单位,建起了68000多家公共食堂。世世代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农民,就这样恍如梦游一般,一步登天跨进了“吃饭不要钱,劳动不计酬”的准共产主义生活。
笔者所在的生产队是原淮安县城郊公社下关大队第五小队。全队有两个自然村50多户人家,130多口人。当时的生产队长叫王兆恒,是土改时期的老党员。由于我父亲读过私塾,当过私人粮行的管帐先生,因此被生产队用为会计,也兼食堂的会计。
食堂的房子是金姓一户人家无人居住的空四合院子,主要建筑是上下两排草顶堂屋加上面东的一排穿堂。该房屋主人自分家分得这处房产后,一直在上海生活,从未回来过。使用这样的房子做公共食堂,这在当时连牲口家具都搞记价入社的大背景下,是一点都不用操心的。
食堂的硬件准备,主要是盘砌起一座两甑一锅的三眼大灶,以及拆除所有房屋的内部隔墙,好放置各家带来的桌椅板凳。这点点杂活,对于处于高度亢奋情绪下的社员来说,是根本不值一提的。已被确定为食堂炊事员的本家“三瘸子”,虽然走路一颠一跛的,但精力充足,嗓门特别洪亮。原定一个星期完成的事情,结果只用了四天就全部就绪了。各家带去的桌椅板凳,齐刷刷地摆满了上下堂屋。我家由于人口较少,正好家里又有一张不大的“半桌”,便带去权充了餐桌。
离食堂开伙做饭还剩最后两天的时候,公社传下话来,按大队组织各生产队队干及食堂工作人员,去离本大队五里远的万友乡参观人家的食堂。我当时年龄小,也远远地跟着人群去瞧了趟热闹。自己虽然看不出什么道理,但从参观回来大人们的谈话中,还是觉出多数人还是很兴奋的。只不过到晚上,父亲回家后,轻轻叹了口气说了句:作孽啊!倒让自己百思不得其解。
我们队的食堂从筹办到9月20日正式开伙,前后一共只用了10天时间。
最拥护吃食堂的是杨小龙
说到集体吃食堂,最兴奋、最好奇的是各家的孩子;但要论谁从心底里最拥护吃食堂,则要数村上的杨小龙。
小孩子天性就是“人来疯”。过去一家一户吃饭,最多也就那么几口人,每天都见面,谈不上什么新鲜感。现在不同了,一到吃饭时间,一百多号人聚在一起,排队打饭的,熟人聊天的,小孩打闹捉迷藏的,加上性急的年青人筷子汤勺的敲击声,这里不谛成了孩子们快乐的天堂。我当时是小学生,处于儿童和青年之间,对于这样的生活方式,自己总体上是很感兴趣的。但时间不长,自己便也从大人们的眼神暗语中,觉出有一些什么不对的地方。
大家背地里嘀咕最多的,就是杨小龙一家。
小龙弟兄三个他排行第二,父亲去世得早,全靠母亲好歹将他们带大。三兄弟最大的18岁,最小的15岁,正是“饭榔头”的年纪。这杨小龙自小到大,除了鼻子下面永远流着两条“黄浓”鼻涕外,唯一让人称奇的就是食量大。
食堂刚开伙时,各家吃多吃少是没有计划的。每次小龙家打来的饭食(主要是玉米面窝头和黑麦面馒头)都要装满一大面盆。炊事员为图省事,窝头都做得特别大。用我妈的话形容就是“有小孩子头大”。小龙一个人一顿要吃4个,且青菜烩粉丝管够。这样的日子在他家过去是从未有过的。
小龙的母亲过日子素来缺少计划,且喜欢玩纸牌,因此全家饥一顿饱一顿几乎成了寻常事。合作社后,小龙也到了劳动力的年龄,但“懒龙”名声在外又加上老气横秋,所以谁都不愿意和他搭档干活。邻里之间帮忙搭个猪圈、屋顶理理草什么的,饭倒是管饱的。但一般人家想想小龙能吃不能做,因而也就没有人愿意请到他帮忙。因此,对于杨小龙来说,哪一天能顿顿吃饱肚子,这一直就是个奢望。
现在,国家号召办集体食堂,实行吃饭不要钱,劳动不计酬,这样的消息,对于杨小龙来说,无疑是太及时、太惬意了!
从一得到办食堂的消息起,杨小龙就几乎没有一天不去食堂的工地上转悠。在大队组织人去万友乡参观食堂之前,杨小龙就提前两天发布了“万友乡食堂泔水缸里都漂的是肉”、“泗阳那边都已经实行十三包了”等对他来说都是极为重要的新闻。
待到食堂开伙后,几乎顿顿饭都是杨小龙家第一个领到饭菜开吃。看着杨小龙家饭桌上如雨的筷子和风卷残云般吃剩过后的残羹,一些平时肚量大点的,只是微微邹邹眉表示厌恶;但一些原本就小鸡肚肠、无事尚且生非的主儿,则时不时地找出茬儿,拉上队干部去小龙家的饭桌上理论一番。理论的内容无非是他家的白菜烧粉丝怎么这么稠啦,凭什么他家的烧土豆吃剩下,我们家来迟一脚就不够吃等等。
队干们碰到这类的事情,总感到十分挠头,多数情况下是把双方都呛白一顿。但呛白归呛白,争吵的双方不到自己都感到嗓门难受支持不下去了,是决不会主动休战的。在我的印象中,唯一一次争吵时间最短的,是我父亲劝架的那回。记得当时父亲说了句:“你们都别吵了,就这样的日子能过长了就不错了!”当时的情景是父亲的话语刚一出口,满屋子的人都静了下来,连争吵的主角杨小龙也怔怔地愣在那里,再没有说出话来。
后来队上集体食堂的发展情势,果然被我父亲不幸言中。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公共食堂的运作方式,就出现了质的变化。
谨小慎微的父亲死在食堂会计任上
管粮管草的父亲,是对食堂的生存现状再清楚不过的。
58年是全国上下浮夸风最盛行的一年。在去公社的路上,随处可见亩产万斤以上的丰产方标志牌簇立在田间。我家祖屋的山墙由于紧挨公路,也被搞宣传的秀才们画上了几枚硕大无朋的花生,并写上一首顺口溜:“花生大王,千人难扛,放在屋旁,压歪了山墙”。在淮阴地区统计的农业生产年报中,58年粮食总产量达到了110亿斤,是上一年已然虚报浮夸下形成的数字的2。5倍,其中淮安县玉米平均单产更是超过了10000斤!而实际的情况是,淮阴地区粮食实收数当年仅为26。7亿斤,与57年实收数相比还下降2。3亿斤!以至省政府在年底前后不得不紧急调运9000万斤粮食支援淮阴。
望着日渐减少的库存粮食,看着公共食堂里丝毫觉察不出半点危机的邻里乡亲,父亲的心都揪疼了。父亲多次向其它队干建议:照目前公共食堂的这种吃法,再大的家当也支撑不了,要尽快实行按人定量打饭;过去我们这里的地主人家,也不见得顿顿饭都吃粮食而不吃一点代食品;田里的庄稼一定要收干净,现在地里的粮食散落的太多了,这样子糟蹋粮食是要遭天报应的!
父亲梗直的话语,虽然得到队里多数社员的赞同;但与当时举国上下盛行的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的大风向显然是格格不入的。父亲的言行很快就引起了公社派驻在大队的社教人员的注意,在数次队主要干部的会议上,该人员多次质问,五队怎么能让这么个有历史问题的人来当食堂会计?父亲为人谦和率真,又识文断字,因此在40年前后,曾被当地民众普选为下关东镇镇长(当时属国民党韩德勤统治的地盘)。由于身负这样的历史包袱,父亲平时的为人处事还算是谨小慎微的。但其率真的天性,又让他在此类是非分明、但却十分敏感的问题上,屡屡暴露出自己城府不深的幼稚。父亲在得知有人查问自己的历史问题后,思虑再三,便向队委会提出了辞去食堂会计的请求。队干们虽然明知我父亲是最最合适的人选,但迫于压力还是同意了我父亲的请求。于是食堂会计的重任落到了我的一个远房堂兄的身上。
堂兄年龄太轻,业务生疏,好玩而又容易冲动,很快就遭到从干部到社员的一致反对,罢黜举措在10天以后就发生了。由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队干们反复权衡,几次三番地找上门来开导和动员,父亲终于无奈地再次回到了食堂会计的位置上。
经过这次的起落变故,父亲脸上的邹纹又深暗了许多。经久不停的咳嗽,使他原本单薄的身躯更显得佝偻的厉害。在对待如何办食堂这个问题上,父亲虽然仍有自己明确的判断,对工作也仍是一丝不苟,但在公开场合,父亲的话语已经失去了往日的鲜明和冲动,多数情况下,更是被沉默所代替。
说不清是客观的情况使然,还是我父亲及其他队干明里暗里的推动,五队食堂在经历了最初的红火之后,勉强维持了不到100天的时间,便宣告取消饭菜管饱、不上计划的做法,而改为按人定量打饭打菜的办法运行。到临近春节时,由于大家对菜的品种口味矛盾太大,队委会再次作出决定,宣布今后公共食堂只负责按人定量供应主食,吃什么菜由各家自行解决。
五队食堂当时的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多数食堂后来都陆续采取的方式。但五队食堂由于实行的比较早,决策人还是承担了一定的风险的。此后,五队食堂就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阶段,直到61年元月彻底解散。
父亲在食堂会计任上,能让我觉出所谓“沾光”的,那就是父亲从食堂里拎回煮胡萝卜水,然后再熬成糖糊糊吃这件事了。食堂锅大,煮的胡萝卜多,捞去胡萝卜后的汁水,里面的甜味就特别浓。回来再一熬,简直比小贩卖的梨膏糖还甜。这就是父亲留在我的记忆中的仅有的一两次“特权”!
60年元旦前夕,父亲咳喘病再次发作。由于当时医疗条件十分有限,为父亲治疗的崔麻子仅是一个乡村医生。他只顾给病人止咳,却不懂麻黄素对神经系统的致命的麻醉后果。结果父亲因被施用了过量的麻黄素,稀哩糊涂地离开了我们,享年仅54岁。
在清理父亲遗物时,除了一把算盘,一本账本,一支水笔,唯一的发现就是一个存折,那是全队社员的所有家当。存折上的余额与账本上分毫不差:6。90元。
我与打饭的木茶桶
自食堂实行按人定量分食制以后,我家每次打饭的任务,就自然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由于我个子小,母亲从家里翻出了祖上传下来的一个木制茶壶桶让我打饭用。茶壶桶比水桶要小,一边还留有一个豁口,是让放在里边保暖的瓷茶壶嘴子伸出来倒茶用的。我家正常三个人的饭,即便是早晚的玉米面粥,也到不了豁口边。
从我家到公共食堂,路程不算远,总在一里半路左右。正常空桶去的时候,我把茶桶的铁把挂在肩上,很轻松地就到了。但回来的半程,可就不那么简单了。早晚的稀粥,打好后离边上的豁口,也就那么不到一寸,走起路来,稍有颠簸,里面的粥就会溢出来。再加上我年纪小,拎上这么个比我矮不了多少的粥桶,本身就比较吃力,茶桶的把子又是细铁丝的,拎的时间一长,手掌被勒得生疼,因此一路上少不了要息上好几回。
打饭的次数多了,我逐渐在沿途确定了几个比较固定的休息点。一处是生产队地头的水车棚旁,一处是北头河边的大柳树下,再有一处是临近祖屋后自留地边的高埂上。选择祖屋后和柳树下面休息,完全是因为路程远近的关系,而选择水车棚旁息脚,却是因为那里正对生产队的一片面积不小的农田。农田里一年四季总有些让人嘴馋的萝卜、瓜蔬之类的作物。而这些作物,对于饥肠碌碌的孩童来说,其吸引力是不言而喻的。
在我的记忆中,我自己也记不清从这块田地中,到底获得了多少带有泥土清香的美食。以至于后来每读到鲁迅先生的《故乡》,读到其中“一轮金黄的明月,挂在深蓝色的夜空。。。”美文时,总会从心底里升腾起一种恍如置身其中的、说不清是美好还是酸楚的感觉。
公共食堂在粮食问题上窘境,很快又从打到我家茶壶桶里的三餐反映了出来。刚开始实行分食制的时候,我清楚地记得打回去的饭、窝头、粥,还能勉强让家人吃饱。一次食堂吃赤豆饭,母亲不在家,是我喂的四岁的小侄女。小家伙吃饭不知道停,只知道饭来就张嘴,结果被我喂得肚子撑得滚圆,几天不吃不喝,直把我母亲吓得不轻。
往后来,窝头越变越小,粥越变越稀。各家各户去打饭的人,也越来越计较炊事员称饭时称杆的高低,打粥时大勺子的水平与否了,三天两头还会有人把已打回家的饭食又拎回来让炊事员重新过称。
待到食堂的稀粥里也出现了胡萝卜,整个农村的粮食问题已经是十分的严峻了。食堂能供应给社员的饭食,几乎只能够一个正常人饭量的一半不到。家家户户都在食堂供应的主食之外,又在家里烧煮了大锅的南瓜、白菜、豆角等充饥。再往后来,瓜菜都被吃光,人们又将目光投向了长在荒田野塘的各类野菜上,其中有不少野菜,过去是连猪都不肯吃的。
我当时的年龄,仅有十一、二岁,我还搞不懂母亲为什么非得要让我顿顿去吃那缺盐少油的萝卜白菜。为了防止我光顾吃主食而不吃代食品,母亲总是尽可能先把萝卜瓜菜等与主食混到一起。记得有一次食堂难得供应米饭,我打饭刚一回来,母亲就让我把大半铁锅的胡萝卜往里拌。我没好气地拿起铁铲就往茶壶桶里一阵猛捣,结果将本来就不十分结实的木茶桶桶底给捣了下来。惹得母亲结结实实打了我一巴掌。事后,母亲让我把桶板、铁匝一件不拉地拿到村西的卜木匠家,从桶底去掉一圈,才勉强修好又继续用来打饭。
吃食堂时期木茶桶与我分离最久的一次,就是60年署假我去乡下姐姐家去那一次了。姐夫当时在本县顺河乡供销社,是个人人眼红的单位,我在那里生活了一星期。供销社也吃食堂,可那里的食堂无论从饭菜的品种,还是数量,都远不是我家里的食堂能比的。最大的感觉就是它那里的菜好像滑爽爽的,特别香(其实就是油水多)。尤其让兴奋的是,到了天黑,夜深人静下来,姐姐还会生起炉子,为我煎上一两个鸡蛋。当我因开学在即将要回家时,姐夫颇费筹措地为我准备了一盘豆饼,这在当时可是紧俏万分的救命之物。姐夫特地找了一个熟悉可靠的蹬二轮车的,将我送回家来。
当我回家拎起木茶桶继续我的打饭活计时,从周围各乡,纷纷传来了公共食堂关闭的消息。五队的食堂由于管理的比较严格,在公社、大队的多次表扬声里,又苦撑了一段时间,直到61年元月,一个特发事件,才让其彻底停了下来。至此,与我相伴了两年多的木茶桶,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特殊使命。
白里透红的炊事员“三瘸子”
“大跃进”时期,人们的脸色普遍是黄灰色外加一丝青绿。长期的营养不良,导致患浮肿病的人也随处可见。在这样的大“背景色”下,如果能碰到一个面色白里透红的人,那绝对是让人侧目的。
“三瘸子”就是这么一个让你惊奇的人物。“三瘸子”本名叫陈凤栖,是我的一个本家堂兄,在家排行老三。小时得过轻微的小儿麻痹症,走起路来一丢一丢的,因此背地里多数人都叫他“三瘸子”。
实行分食制之前,“三瘸子”的肤色与大家都差不多,在众多的男人中间,他只能算是“不黑”而已。“三瘸子”小时候上过几天学,人又非常的精明,队里开始筹办食堂时,就被指定为食堂的炊事员。
“三瘸子”对待食堂的公家事情,那是没什么可说的。前面提到的食堂垒灶拆墙等事项,“三瘸子”在里面领头协调,既能说又能干,队里上上下下,没有不佩服的。待到食堂正式开张起来,全队百十号人的吃饭头等大事,更是让“三瘸子”的办事才能得到了充分的展示。每顿饭需要多少粮食下锅,油盐酱醋各要添买多少,“三瘸子”一般情况下都是一口清。在碰到有些开支较大需要队干们集体拿主意的问题时,“三瘸子”经常能在关键时刻,用他那洪亮而又斩钉截铁的话语,起到一锤定音的作用。久而久之,“三瘸子”虽然在职务上仅是食堂的一名炊事员,但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影响、风头几乎已经盖过了除正副队长之外的其它队委,俨然有了队里“三把手”的气象。
就在“三瘸子”的威望与日俱增的关键时刻,他与普通人群面色上的差异,无声无息地扩展为阻止他威信进一步提升的巨大横沟。
吃食堂初期,人们对灾荒可以说完全没有准备。终日的紧张、狂热,没有人去分辨谁的肤色怎样怎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年累月备受饥饿煎熬的人们,终于从肌体感觉之外的肤色上读出了灾荒留在人们身上的印记。当人们在某一天早上,突然发现在一大堆灰暗青绿的面孔中,竟然有一张白里透红的面容时,就好象猛然找到了导致自己饥饿的原因,于是立时便把所有的愤恨和不满都发泄到这张面孔上:
多吃多占首先是“三瘸子”确定无疑的罪名,那张白里透红的脸就是铁证;打饭“看人兑汤”严重不公,包庇家人队干部,这项罪名,说的人不少,但真要拿出实据来,也还不那么容易;作风不正,漂亮的女的来打饭,就保准多打。这一指责,虽然有时连传的人自己都有些胆虚,但却传的最广。一时间,“三瘸子”的这些传闻,几乎成了五队社员家前屋后的所有谈资。
最先向“三瘸子”公开发难的,是杨小龙母亲。那天我在食堂打饭还没走,杨小龙的母亲就一路骂骂咧咧地闯了进来,上去就将小龙刚打回去的饭食往称饭的铁皮盘子里一放,喝叫“腿瘸眼也瞎”“三瘸子”自己看称。“三瘸子”对杨小龙母亲一贯的骂街行径是司空见惯的,但这一回,对方将骂街矛头直接冲向自己,这还是第一次遇到。从称星上看,打给小龙家的饭食份量是不足。但精明过人的“三瘸子”立刻就作出了回击:打出去的饭是热的,水气跑了还能不轻一些?再说小龙路上谁能保证没偷吃!争吵到最终的结果,是别的炊事员从锅里象征性地又补了小龙家一团饭。
有了这一次的开头,无边无际的猜疑和责骂就象原本张开在黑暗中的蛛网,突然被猎物搅动,一下子有了明确的目标,炊事员“三瘸子”几乎成了五队社员人人口诛挞伐的靶心。
说来也怪,在五队食堂里做事的人员,连“三瘸子”在内,也有三、四个人,为什么大伙不向别人发火,却偏偏都向“三瘸子”发?其实,说穿了这里的原因也简单,一是因为“三瘸子”在食堂里是个主事儿的;二就是“三瘸子”腿虽瘸,但吸收消化功能好,多吃了点,全放在了脸上,让人一目了然。
也有人算计着想将“三瘸子”的炊事员职务顶掉,但所提动议根本就没法上队委会研究。这倒并不是因为“三瘸子”打饭将队干们侍候得好,而是因为这时全国农村的大办食堂形势已经出现了明显的逆转,不少地方的食堂已经先后关闭。而五队食堂却一枝独秀,多次受到公社、大队的表扬,“三瘸子”有功于斯。再说,谁做炊事员都要多吃点,已经养肥了一头猪,还要再做冤大头去喂一头饿虎?
于是,“三瘸子”终于以他那白里透红的“另类”脸色,伴随五队食堂走完了全部历程。食堂解散后,更严酷的大灾荒继续揉躏着中国大地,“三瘸子”也很快回归到面色青黄的人群中。
一场大火让公共食堂寿终正寝
就在五队食堂维持着外表风光,仍然在艰难地运转之时,全县、全地区乃至全国农村脆弱的粮食基石,终于经受不住大跃进、浮夸风、瞎指挥三股邪流的轮番侵袭,无可幸免地瘫塌了。
最早从外县传来的让人震惊的消息,是泗洪农村上万人饿死的“泗洪事件”;紧接着又从更远的安徽农村传来“老鼠吃人”、“人吃人”传闻。一时间,村上的大人小孩,几乎人人陷入了一种惶惶不可终日的状态。市场上除了黑市粮食紧俏外,金银首饰的价格低到了惊人的地步。一付金耳环,换不来20斤玉米。一个普通教师一个月的工资,买不到一袋山芋。“五级工,一担葱”,更是当时社会上流传极广的形象哩语。我偶尔一次进城,看到当时淮安县最大的国营饭店“淮安饭店”贴出的营业招贴,上写“高级饭”一桌108元(相当于一个普通教师四个月的工资),主食竟然是黑麦面馒头!
还有让淮安老百姓至今仍感叹不已的消息:淮安县委书记李仲英,因抵制浮夸风下形成的高征购,宁愿去省城受处分,也不让再从淮安调出粮食,结果人被逼疯,因此失去了工作能力。
上述的所有传闻,经笔者事后至今的查证,都是真实的。其中泗洪饿死人事件,其饿死人总数竟达到17256人。另外,泗洪还有51529人患浮肿病,占当时泗洪人口总数的9%以上。对县委书记李仲英,笔者在与年岁稍大的干部教师交谈时,经常听到他们发至内心的称其为“李青天”。一任县委书记,能在其隐出政坛数十年后,仍在干部百姓中拥有如此的口碑与威望,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
笔者所在的城郊公社下关大队,与上面所记述到的地方相比,情况要稍好一些。但社员群众在食堂供应的饭食之外,所用来充饥挡饿的物品,至今天罗列起来,仍然是让人感到十分震撼的:除上面提到的白菜、胡罗卜、南瓜、豆饼、野菜之外,萝卜英子、山芋叶子、榆树皮、扫帚柳叶子等,均是各家常见的食物。稍有一点门路的,能从豆制品厂找人批条子买来豆腐渣,能从酒厂买来酿酒后的剩余物山芋渣,则在当时绝对算得上是罕见的奢侈食品。与五队仅一河之隔的螺丝村,生产队管理比较混乱,社员的生活就显得更为凄惨。其中有一户马姓社员,一家四口全部患上浮肿病,由于饥饿难忍,就从地底挖掘一种叫“观音土”的河泥充饥,结果吃下后连屎都拉不下来。
五队的食堂就是在这样芨芨可危的大环境下,艰难地支撑到了61年的元月份。
当我得知食堂失火的消息时,已经是第二天的打早饭时间。母亲见我揉着惺松睡眼正在摸弄木茶桶时,对我说:“今天不要去了,食堂夜里失火已被烧光了”。
听了母亲的话,我一下子怔住了,放下茶桶,便向食堂的方向跑去。老远就见食堂的屋基处,已是一片废墟。大队、小队的干部都在那里,还有穿公安制服的人在废墟上丈量察看着什么。在废墟一角,原在食堂专管烧火并负责守夜的金二爹,一脸惶恐地呆坐在那里,两眼无助地望着在现场察看的干部们。
事后听大人们传说,现场堪查没有发现人为纵火的痕迹,食堂失火的原因,是金二爹头天夜里的灶火没有清理干净造成的。
就在各家都在为食堂没了,忙于到队房里去领口粮时,一声尖厉的警笛,打破了小村的宁静。紧接着,一阵零乱而杂沓的脚步声响到了屋后,有人高喊着:公安局来抓人了!我和母亲连忙循着喊声跑过去,只见一辆土黄的警车停在路边,两三个公安人员正架着金二爹向车上走去。原本就比较木纳的金二爹,此时已失去了行走的能力,几乎是被拖架着弄上车的。
这就是家乡的公共食堂留在我的印象中的最后一张记忆截图!
由于五队食堂是全公社乃至全县都数得上的样板食堂,就这样毁于一场大火,因此金二爹被判了在三年徒刑。
苦涩的记忆已然十分的久远,我真的不想在再回到这段让人心酸的往昔中去。
2006。08。05。
12下一页
来源: https://sanwen.aiisen.com/sanwen-231834/更多资源请访问: https://sanwen.aiisen.com/sanwe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