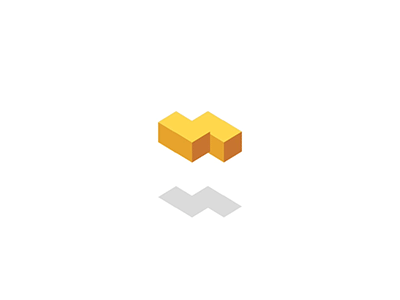+-


40年前,初春的夜上海,一座普通居民楼里,一个大一的年轻人在他未婚妻家的小阁楼上熬夜写作。当最后的标点落下,泪水已经濡湿了脆薄的纸张……让他怎么也想不到的是,这篇用心凝成的小说,日后会成为划时代的惊世之作。
这篇被《文汇报》破例整版刊登的让“全中国的读者泪流成河”的作品名叫《伤痕》。这个叫卢新华的24岁的复旦大学中文系学生,几乎一夜成名。
岁月不居,40年弹指一挥间。这位耆年硕德的“伤痕文学”之父,在《伤痕》发表四十周年之际,带着他浓缩数十年人生精华的《三本书主义》回到家乡。
偌大的新华书店被围得水泄不通。那晚,写完《伤痕》搁笔的那一刹那,脑海里只有一个念头:“我可以死了,我已经完成了我的使命。”读者见面会上,先生谈起《伤痕》创作时,说出的这句话如惊雷般响彻在我的耳边。
是啊,在上世纪那个特殊年代里,“三突出”文艺创作模式的提出,严重束缚了当时文艺作品的创作,文学的枷锁,发展成了人们“心灵的枷锁”。如今,在这样一个开明开放的新时代,我们如何能够彻底摆脱这样的枷锁,让心灵自在呢?
现场互动提问时,我站起来大胆地向先生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是的,我们人生路途中真正的‘枷锁’是什么呢?那就是‘财、色、名、食、睡’五毒”,先生微微一笑,似乎心中早就有了答案。接着他又娓娓讲述起他在云南采风时的一些感受:“我在一次万人跳舞活动上看到一群老太太在跳着具有彝族特色的‘玛咕舞’。她们扭腰、提腿、踮足……什么动作都做得有板有眼,我很是好奇,就问一个老太太:“你们这样通宵达旦地跳,第二天还要干活呢,难道不累吗?”而老太太的回答令我意想不到:“就是因为累才跳的呀!”我惊讶之余,再去观察她们跳舞时的模样,都是眼睛微闭,面容宁静祥和,跳的过程中就像整个心灵都睡着似的。
现场一片宁静,人们似乎都深受感染。先生接着讲述起他四十年创作生涯以及“三本书”里各自所蕴含的深意。他说,“有字之书”是指中外经典的文学著作;“无字之书”则是去读自然与社会,需要去“行万里路”;而“心灵之书”则是“人的心灵的观照、反省、体悟”,让心自由,让灵魂自在独行……
第二天,得知先生在接受家乡电视台的专访后有一个短暂的空隙,我萌生了向这位文学大家当面请教的大胆想法。在家乡作协一位热心长者的帮助下,我终于得以与先生进行了面对面地交流。
“你叫肖筱萌,我记得你……”先生的热情,一下子消弭了我的紧张情绪。我还是很不好意思地拿出了自己的三篇拙作,恳请先生能抽出宝贵的时间粗略一读,并能提出批评意见。先生接过稿子,不紧不慢地先抿了口茶,就开始按次序一行行地仔仔细细地往后看。约莫二十分钟后,先生开始把目光移向我,朝我赞赏地点点头:“嗯,写得很好!”我一愣,心脏在“咯噔”一跳后开始雀跃起来。“文章很有禅意,可以看出你的境界挺高的。”随后,先生又亲切地问起了我的年龄、学业情况。他希望我将来不要被社会上的世俗所影响,安静创作,假以时日一定会有所造诣。我脸一红,看到先生赞许的眼神,激动得有点语无伦次……
正在我准备告辞之时,先生忙把手掌向下摆摆:“不急不急,我还要留一道题目给你呢。”
连喝了几口水,先生清清嗓子慈祥地对我说:“狼山你去过的吧,”我顺势点点头,“那么,你注意到广教寺的那副对联了吗?”我有些难为情地摇摇头,“清代通州知州平翰写的:‘长啸一声山鸣谷应,举头四顾海阔天空’,我个人觉得不怎么对仗,禅意少了些,你能把它改得更好些吗?”,“我把邮箱留给你,改好了你发给我。”
与先生道别后,在回家的路上我想了很多,迫不及待想要找到答案。
第二天,在父母的陪同下,我专赴狼山,再游广教寺。
拾级而上,门首石柱上的那副对联很快就映入眼帘。殿内香雾缭绕,钟鼓之声不绝于耳,信步走到门口的大观台,放眼南望,水天一色,烟波浩渺,山色风光尽收眼底,再仰视天空,顿有高入云端之感。
没有更多的心情赏景,我体悟着先人平翰当年作此对联时的心境,不禁思忖:当年这位功底深厚的大家在此作诗时究竟疏漏了什么,让一百多年后的这位智者发现瑕疵。
远眺着江面,我脑子里蹦出了好几种改法:抚琴长啸山鸣谷应,抬头远眺月照江粼。忽然又觉得不对,虽有些对仗了,也保留了原对联的基本意思,但时间跨度上,因为有了月照一词,时间就到了晚上,还自作主张搬来了古琴,这样改有违事实,不妥。转念改为:抚琴听涛一眼江天,举杯邀月万古烟云,看上去对仗了,但还是有问题,抚琴时还在听涛可怎么抚琴啊?
折回的路上,我依然苦思冥想,横竖难得其解,我不断追问自己:是不是因为太想找到答案了而偏偏难以找出答案?是不是因为自己太过稚嫩而厚重不够?
虽没能找出答案,但这次未能完成的作业却让我顿悟:人生需要不断登山,登高才能望远;人生亦需时常下山,下山才知卑微。只有这样,才能读透先生所说的从有字到无字到心灵的人生三本大书,寻到属于自己的那份甘泉。
相信终有一日,我会找到那合适的答案,给先生发去邮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