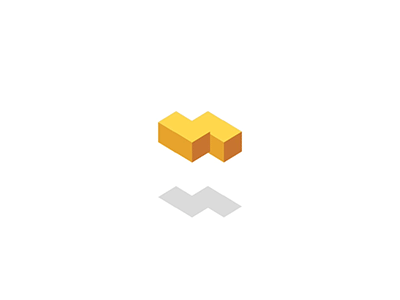5.握手渝州
一
1945年8月28日下午,73岁的张澜在重庆九龙坡机场焦灼地等待着。他的身旁,还有特园主人鲜英与黄炎培、冷御秋等。
过去几个月尤其是一个月来的形势变化,超出了所有人的意料,带来了普天同庆的狂喜,也给明眼人们带来新一茬的近在咫尺的担忧。
8月6日,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月8日,苏联宣布对日宣战,苏联红军进入中国东北,向日本关东军发起猛烈进攻。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这一天,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8月14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用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向日本民众宣布无条件投降。至此,历时8年有余的全面抗战,以加速度的、摧枯拉朽的方式划上了句号。
举国欢欣鼓舞。饱经沧桑的张澜老泪纵横,他对特园主人鲜英说:“从‘七七’算起,今天是八年零三十二天,从‘九一八’算起,今天是十四年零三十七天,日本残杀我同胞不计其数。虽说天网恢恢,侵略元凶终归殄灭,但死者又岂可复生?胜利来之不易,希望国民党好自为之。”心有苍生喜亦忧。实际上,在8月初,他就作出了这样的诗句:“党权官化气飞扬,民怨何堪遍后方。且漫四强夸胜利,国家前途尚茫茫。”[53]
可见,太熟悉蒋介石本性的张澜,已提前预料到,抗战胜利后的主要矛盾,将是国共矛盾,或者说是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与全国人民的矛盾。这一场风暴,虽与抗日的性质不同,但何尝不可能又是多年的血雨腥风?那么,局势会怎么发展,国家的前途又在何方呢?
张澜的忧虑,完全是基于现实。除了国共之间的纷争在抗战胜利前夕没有消停过,他本人与国民党的矛盾也并未消弭。
在中共七大之后,1945年7月7日,国民党参政会四届一次会议开幕。实际上,为了夺取讨论国民大会问题的话语权,在当年4月,国民党单方面修改了参政会组织条例,将参政员由240名增加到290名,新增者几乎全是国民党员,以便在7月会期审议通过于当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的决议。为此,中共发表声明,中共参政员将不参加这次参政会。民盟内部没有采取统一行动,左舜生准备出席,黄炎培等表示可以出席、但绝不参加有关国民大会的任何讨论,张澜则表示坚决与中共共进退,不参加这次参政会。[54]针对会前一些无聊小报对自己的污蔑,和参政会上黄炎培等所受的侮辱,张澜再次致信蒋介石,敦促其为政秉持“诚与明”。
二
抗战胜利前夕的民盟,非常活跃,期间发生了一段足以载入史册的对话。这便是著名的“窑洞对”。
为了调解国共矛盾,同时也为了加深对中共的了解,7月1日,参政员黄炎培、褚辅成、冷遹、左舜生、傅斯年、章伯钧经蒋介石同意,飞往延安,进行了为期5天的访问。归来后,黄炎培写出了著名的《延安归来》,以其细腻而敏锐的视角,简练的语言,对延安之行进行了描述。这本小册子无异于大后方的一声惊雷,让长期接受国民党媒体对中共丑化宣传的大后方群众,有了一个客观认识中共的机会。
《延安归来》写道:“现在延安有5万人口,其中3万多是公教人员和他们的家属等。这种人员,不论男女都穿制服,女子学生装短发,都代表十足的朝气。”“料不到,这几位先生(编者:贺龙、彭德怀、聂荣臻、林彪、刘伯承等将领)都是沉静笃实中带着些文雅,一点没有粗犷傲慢样子。真是出于意外。”“只觉得一切设施都切合一般的要求,而绝对不唱高调,求理论上好听好看......这是事事有组织、人人有训练的缘故......没有一寸土是荒着的,也没有一个人好像在闲荡。”“延安五天中间所看到的,当然是距离我的理想相当近的。我自己也明白,因为他们现时所走的路线,不求好听好看,切实寻觅民众的痛苦,寻觅实际知识,从事实际工作,这都是我们多年的主张......集中这一大群有才有能的文人武人,来整理这一片不小也不算大的地方,当然会有良好的贡献。我认为中共朋友最可贵的精神,倒是不断地要好,不断地求进步,这种精神充分发挥出来,前途希望是无限的。”[55]文中写道,在毛泽东接见这一行的会客室里,还挂着由沈钧儒之子沈叔羊作画、黄炎培题词的一幅有关茅台酒的作品。这当然让黄炎培感到惊讶而亲切,足见中共用心之细。
而“窑洞对”,则是后人对这一段对话的概括:
有一回,毛泽东问我感想怎样?我答:“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因为区域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56]
这段对话,至今仍发人深省、散发光芒,鞭策警醒无数的后来者。
三
《延安归来》的火爆,阻止不了国民党发动内战的行动。7月参政会刚刚闭幕,国民党便调集了几个师的兵力,突然对陕甘宁边区发动大规模的进攻。[57]
7月7日,民盟云南省支部为纪念抗战八周年发表“敬告国人书”;7月28日,民盟发表“对时局宣言”;8月3日,张澜以民盟主席名义在招待外国记者会上发表谈话;8月12日他发表对抗战胜利结束的谈话;8月15日民盟发表“在抗战胜利中的紧急呼吁”。这一系列声音,都严肃谴责内战,呼吁成立联合政府,并坚决抵制国民党企图包办的国民大会。笔虽不如刀,檄文皆似箭。
以上言论指出:“在八年的苦战期中,因负责当局在经济财政政策上的错误,致令人民牺牲了如许生命财产,结果只养肥了一个官僚资本和发国难财的集团,而这个集团无疑的将必继过去列强经济侵略的后尘,来压迫中国大多数人民的经济生命。并且今天十分之九的人民已成赤贫,抗战胜利的来临,眼看要赶不上国内经济崩溃的速度。”
“抗战胜利还只是在望,内战的险象已经环生了,反攻的战略还没有开始,新式装备已经用来自相残杀了。”
“今天中国正站在十字路口,我们看得见胜利,又看得见崩溃;看得见复兴,又看得见衰落;看得见生长,又看得见毁灭;看得见光明,又看得见黑暗。”[58]
“假如我们国家在胜利之后,仍不能以民主方式统一建国,那真太不成话了。”[59]
“今后一切的党派只有事事为着人民采用光明的前途,我们现在正是以人民的名义向你们发出热烈的呼喊,请你们千万不要忽视。”[60]
从这些堪称经典的有锋芒的文字中,我们能感受到当年局势的紧迫。当时,国共矛盾的一个焦点,便是对日军的接收问题。
抗日战争即将结束之时,中共军队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分割着日军,处在全国受降的第一线。而蒋介石的主力则龟缩于西南大后方。这就意味着,如果允许日本向中共投降,那么中国将很快成为共产党的天下。因此,当中共下令对日寇全面反攻时,蒋介石立刻使出了手段,于8月11日发出三道命令:“(一)国民党军队‘积极推进’;(二)电延安朱德、彭德怀,要中共部队‘原地驻防’;(三)伪军‘维持治安’,岗村宁次不得向国民党军以外的部队投降。”[61]为了加持这一荒诞命令,8月12日,麦克阿瑟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命令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只能向国民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人民的武装力量缴械。可见,在美蒋眼中,宁可放心让日伪“维持治安”,也决不能让战功卓著的人民军队接管中国的领土。试问,若日伪可以“维持治安”,还需要抗日做什么?为此,毛泽东在《解放日报》上发表评论,予以针锋相对的驳斥。
在受降的角逐中,一个最敏感的区域,便是东北三省。这是曾因蒋介石不抵抗政策而丢失的土地,是杨靖宇、赵一曼等共产党人浴血奋战的土地,也是被苏联红军接管的土地。对于中共而言,因国民政府即将还都南京,如果说南方是蒋介石的大本营,那么面对国民党的大兵团围剿,东北就将成为中共的战略命脉。中共随后形成“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并向东北秘密派遣军队,就是基于对东北的准确认识。蒋介石亦极为重视东北,他认为手中握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王牌,按照条约,苏联不会支持中共。
此时的中国,成为美苏、国共三国四方关注的焦点。抗战胜利,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呼声高涨。美苏出于自身利益考量,也声言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特别是国民党部队调动兵力尚需要时间,蒋介石感到发动内战的时机还不成熟,于是大造和平舆论,[62]这就成为了重庆谈判得以发生的重要原因。
四
1945年8月14日起,蒋介石三次致电毛泽东,邀请他到重庆举行谈判。蒋氏的如意算盘:毛泽东如拒绝到重庆,即可证明中国共产党对和平没有诚意,国内外舆论必然谴责中共,武力解决共产党亦有了借口。而如果毛泽东来重庆,则在谈判桌上压迫中共,以让延安派几个人到政府做官为代价,诱逼中共交出军队和解放区,演一出鸿门宴。即使中共不为所动,也可以借谈判之名拖延时间,调集军队,部署内战。[63]
鸿门宴已摆好。毛泽东为顺应民心、争取主动,以战略家的大智大勇,毅然决定前来。在前来之前,他也已做好了最坏的准备。
就这样,8月28日下午,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的陪同下,抵达重庆。发表完简短演讲后,他穿越过记者的包围,与迎接他的代表们握手。他一下子就认出了等候他的长者张澜,而这实际上是他二人第一次见面!
“你是张表老?你好!”毛泽东问候道。“润之先生好!你奔走国是,欢迎你光临重庆!”张澜说。毛主席握住张澜的手,久久不放,说:“大热天气,你还亲自到机场来,真实不敢当,不敢当!”二人同声称“神交已久”,寒暄开来,周恩来也绕过来同张澜握手,互道阔别。王若飞等亦视张澜为师辈,执礼甚恭,握手言欢。[64]
8月30日上午,刚抵达重庆的第三天,毛泽东即嘱周恩来亲自前往特园,告知张澜,当天下午他将亲自到访。真是贵客将盈门。张澜、鲜英喜出望外,称“我们去拜望他才是,不应劳他过访。”在周恩来的提醒下,张澜等人提高了安全警惕,将会谈地点定在了张澜卧室,因为特园旁边就设有戴笠的特务监视点!下午,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来到特园,与张澜、鲜英促膝而谈。他首先转达了朱德总司令对老师的问候,转达了吴玉章对老友的问候,氛围使人如沐春风。
张澜虽能理解毛泽东到访重庆的用意,但还是非常担心毛泽东的安全。他说:“蒋介石在演鸿门宴,他哪里会顾得上一点信义!前几年我告诉他:‘只有实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他竟威胁我说:‘只有共产党,才讲实行民主’。现在国内外形势一变,他也喊起‘民主’、‘民主’来了!”毛泽东说:“民主也成了蒋介石的时髦货!他要演民主的假戏,我们就来他一个假戏真做,让全国人民当观众,看出真假,分出是非,这场戏也就大有价值了。”张澜说:“蒋介石要是真的心回意转,弄假成真,化干戈为玉帛,那就是全国人民之福呀!”毛泽东向张澜详细地介绍了解放区的开创和建设情况,解释了中共中央八月二十五日《宣言》中提出的六项紧急要求。张澜连着说了几声“很公道”,并且说蒋介石要是良知未泯,就应当采纳实施。[65]
好一个假戏真做!毛泽东确实把云谲波诡的重庆之行,变成了一次广交朋友、传播共产党主张的统战良机。夜间,他处理延安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白天,他在谈判之余脚步不停。看来要反客为主了。
当晚,张澜出席了张治中在桂园为欢迎毛泽东来渝的宴会,期间,毛泽东又抓住时机与沈钧儒、黄炎培、柳亚子、陈铭枢、王昆仑、冷遹、章伯钧、张申府、王云五、傅斯年等进行了商谈。
9月2日中午,张澜以中国民主同盟名义,在特园欢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在渝的民盟主要领导人黄炎培、沈钧儒、张申府、冷遹、左舜生、章伯钧、罗隆基等都前来作陪,济济一堂。一进特园,毛泽东高兴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了!”
“民主之家”,是大家对特园的别称,也符合其内涵,冯玉祥曾亲笔书写这四个字,将美誉高悬于特园二门之上。[66]毛泽东勉励大家道:“今天,我们聚会在‘民主之家’,今后,我们共同努力,生活在‘民主之国’。”热情的主人拿出了珍藏多年的枣子酒款待远方来客。
由于民盟中央领导层较为复杂,出席者三党三派都有,毛泽东除了反复强调“和为贵”之外,以话家常居多。他和沈钧儒谈健身运动,和黄炎培谈职业教育,和张申府话五四运动......家人般地恳谈,其乐融融。宴毕,特园主人拿出纪念册,毛泽东题下“光明在望”四个大字。[67]
五
毛泽东重庆之行中,还与当时已经是民盟盟员的柳亚子有一段有关《沁园春.雪》的佳话。
柳亚子是1944年加入民盟的[68],但他早在多年以前就声名煊赫。1909年他就是筹备辛亥革命的核心文化组织“南社”的发起人之一,1926年作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他已与毛泽东有了第一次会面,这便是我们后来熟知的“饮茶粤海未能忘”。1941年他因在皖南事变后痛斥蒋介石卑劣行径,遭到开除党籍的处罚。8月30日,拜访张澜的同一天,毛泽东在住地会晤了柳亚子。会晤归来的柳亚子,激动不已,写下了诗句:“阔别羊城十九秋,重逢握手喜渝州。弥天大勇诚能格,遍地劳民乱倘休。霖雨苍生新建国,云雷青史旧同舟。中山卡尔双源合,一笔昆仑顶上头。”[69]这大气恢弘的诗句,把历史定格在了那个瞬间,其中气象似已暗示着几年后的结局。
应柳亚子的要求,毛泽东在10月7日将一封信托人交给了他,这便新录的1936年旧作《沁园春.雪》。当时,因为各种考虑,该作品并未直接发表,报纸上只是发表了柳亚子的和词。但这已引发了读者极大的兴趣,《沁园春.雪》还是在大后方流传了开来,11月14日首次见刊,此后又被《大公报》刊登。[70]《沁园春.雪》极富文采、别具一格,指点古今、气势非凡,展现了共产党人的文化自信和宇宙观,让大后方长期对中共有误解或欠缺了解的文人、群众一睹中共领袖的才情和胸怀。它产生了意想不到的极佳影响,堪为争取人心的绝妙一笔。蒋介石极为震怒。
毛泽东访特园时还有一个细节,他在楼梯底下和雇工一一握手问好,那些工人中还有刚刚烧完火的,手脏得很。张澜看到毛泽东的动作,一怔。事后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也是贫寒出身,高高在上几十年,染了一身士大夫气。”毛泽东这样平等对待家里的雇工,张澜感慨万分。[71]与毛泽东会谈后,他由衷感叹道:“得天下者,毛泽东!”
历史无言。但有些历史时刻,可以为后面的历史预言,成为先知时刻。
未完待续!
注释:
[]53.《张澜与中国民主同盟》,广东人民出版社,戚如高、潘涛著,2004年5月第一版,第127-128页。
[]54.《张澜与中国民主同盟》,广东人民出版社,戚如高、潘涛著,2004年5月第一版,第119页。
[]55.《黄炎培与毛泽东周期率对话——忆父文集》,人民出版社,黄方毅著,2012年11月第一版,第317-337页。
[]56.《黄炎培与毛泽东周期率对话——忆父文集》,人民出版社,黄方毅著,2012年11月第一版,第336页。
[]57.《中国民主同盟七十年》,群言出版社,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2011年5月第一版,第19页。
[]58.《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2012年9月第一版,第41-42页。
[]59.《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2012年9月第一版,第53页。
[]60.《中国民主同盟历史文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会编,2012年9月第一版,第56页。
[]61.《抗日战争时期国共关系纪事:1931.1-1945.9》,中共党史出版社,黄修荣编著,1995年8月第一版,第521页。
[]62.纪录片《挺进东北》第一集,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国家开发银行联合出品,央视网,http://tv.cntv.cn/video/C10389/c320b10a8c58485a809791401df2fa56。
[]63.《张澜与中国民主同盟》,广东人民出版社,戚如高、潘涛著,2004年5月第一版,第130-131页。
[]64.《重庆风云》(读.党史;8),中共党史出版社,陈海平主编,2012年1月第一版,《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吕光光著,摘自《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65.《重庆风云》(读.党史;8),中共党史出版社,陈海平主编,2012年1月第一版,《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吕光光著,摘自《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66.《民盟史话》,群言出版社,赵锡骅著,2014年12月第一版,第29页。
[]67.《重庆风云》(读.党史;8),中共党史出版社,陈海平主编,2012年1月第一版,《毛主席同张澜的会见》,吕光光著,摘自《重庆谈判纪实》,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
[]68.《聆听岁月的脚步》,上海三联书店,王海波著,2015年1月第一版,《柳亚子与民盟》。
[]69.《重庆风云》(读.党史;8),中共党史出版社,陈海平主编,2012年1月第一版,《<沁园春.雪>与重庆谈判》,怡青著,摘自《光明日报》2011年6月23日,收入该书时有删节。
[]70.《重庆风云》(读.党史;8),中共党史出版社,陈海平主编,2012年1月第一版,《<沁园春.雪>与重庆谈判》,怡青著,摘自《光明日报》2011年6月23日,收入该书时有删节。
[]71.《张澜:从“川北圣人”到共和国副主席》,王晓莉著,中国共产党新闻网,2013年2月5日,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3/0205/c85037-20441201-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