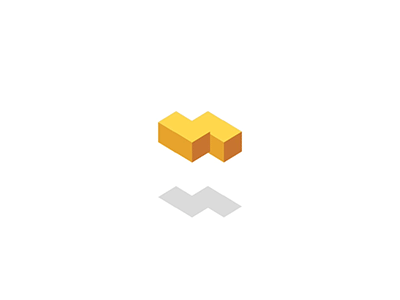华夏、中国、中华,这三个名称是有来头的,也是历史沉淀形成的。
我们的大历史,自夏代才清晰一些,在夏之前,因无史载,基本上是飘飘渺渺的传说和臆想。夏代先人的生活方式开始定居下来,以农耕和城居为主。当时的社会生活就是两件大事,农业生产和筑城而居。农耕,水是重要的,因而夏代重视水利,大禹治水的故事一直流布至今。夏代不仅重视大河的有益有效治理,也看重小流域的保护。《论语》说到禹功,“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轻楼堂馆所重水利命脉。我们今天也重视河流治理,但治理的方式问题太大,黄河被治理得时而断流了,更多的小流域干涸现象已十分严重和迫切。
筑城而居始自夏代,开启了古代城邦的雏形。史载有“鲧作城郭”“禹都阳城”。阳城不是地名,指在山南或水北筑城。城中之地称为“国”,住在城中的人即为“中国人”或“中国民”,简称“国人”。《说文》是这样存义的:“夏,中国之人也。”这时期的“中国”意为“国中”,用以区别游牧民族。

西周上承商代,但因袭夏,以夏为称号,周代辖域内的土地称为“区夏”“有夏”“时夏”,“区夏”即“夏区”,“有夏”中的“有”是语助词,这种表述习惯今天也有痕迹,如葛优做的那个广告,“我有吃”。“时夏”的“时”为“是”,古代表述文字里常见,即“这个”之意,史载有“用肇造我区夏”(《尚书》),“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尚书》),“我求懿德,肆于时夏”(《诗经》)。
西周分封建国,最多时分封了八百多个诸侯小国家,这些小国总称为“诸夏”。“戎狄豺狼,不可厌也;诸夏亲昵,不可弃也”(《左传》)。周王东迁洛邑(洛阳)后,王室的权威下挫,诸侯国之间频繁兼并,列强国家出现,个别诸侯国做大做强,支流漫过主流。这一时期的“夏”限指中原地区,“居楚则楚,居越则越,居夏则夏”(《荀子》),此时,“华”字开始用于文字表述中,“推演出一个‘华‘字来,按华字古音敷,夏字古音虎,其音相近,增用一个字有加重语气的作用。二字可单用,亦可以合用,夏和华二字互举为文,与裔和夷二字互举为文相同”(王树民)。《左传》里的记载有“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楚失华夏,则析公之为也”“今而始大,比于诸华”“诸华必叛”“获戎失华,无乃不可乎”“我诸戎饮食衣服不与华同”。华夏两字并称,在春秋时期就有了,但使用之初,是指中原一带,或有中原地区生活方式的地方。

春秋之前,涵盖我们国家地理全范围的词并不固定,史载有“禹甸”“禹迹”“禹域”“天下”“四海”“九州”“九有”“九域”“九隅”等,这些词都有些含糊,不够明确具体。选取典籍里记载的我国地理全境的三段文字:
“自恒山至于南河,千里而近;自南河至于江,千里而近;自江至于衡山,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东海,千里而遥;自东河至于西河,千里而近;自西河至于流沙,千里而遥。西不尽流沙,南不尽衡山,东不尽东海,北不尽恒山,凡四海之内,断长补短,方三千里。”(《礼记·王制》)
“凡四海之内,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有始览》)
“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管子·地数》)

以“中国”为我国的通称,自汉代开始,“中于天地者为中国”(扬雄),“中国”一词的内涵也有分别,统一时期指全国疆域,分裂时期指中原地区。“中华”一词也在这一时期开始被使用,“中华”一词最早使用是用在天文方面,“东藩四星,南第一星曰上相,其北,东太阳门也。第二星曰次相,其北,中华东门也。第三星曰次将,其北,东太阴门也。第四星曰上将,所谓四辅也。”(《天文经星·中宫》)以人世间的宫城比拟天宫的构造,东西两面各有三个门,中间之门以“中华”命名,在“中国”与“华夏”两词中各取一字,两侧以太阳门、太阴门命名。后世的皇帝也有借“奉天意”之名以“中华门”命名宫名的。
华夏、中国、中华,如今指的是我国全境,这三个词,不仅是地理层面的,更深一层的价值在文化沉积方面。
本文作者穆涛,系《美文》杂志副主编,一级作家,西北大学中文系兼职教授。